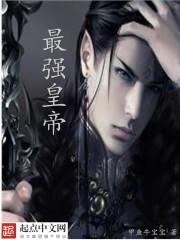趣书网>全天下都知道夫君爱她 > 第369章(第1页)
第369章(第1页)
于是才酿成了相城陷落之耻辱。
如今李衾才带兵返京,本来传言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另生波折,所以兵部侍郎不敢将详细情形告知李持酒。
谁知李持酒别的方面儿一般,在打仗方面却非常内行,一听就察觉不对:“我在那里的时候就知道,当初李尚书定下的规矩,边塞数城是守望相助的,一旦有变就发狼烟,报信号,偌大的一座城怎么会轻而易举给人得了去,难道其他城里的人都是死了的?还是故意的不作为?”
左侍郎见瞒不住,忙向着魏中书打眼色求救。
魏中书道:“皇上息怒,恐怕是那些人大意了,为今之计只赶紧想法子亡羊补牢。”
“什么亡羊补牢,丢了就是丢了,给人踹到脸上我可不知怎么补。”李持酒恼怒之极。打仗方面他向来最为争强,如今竟吃了憋,还是自己的那一派人……他如何受得了。
“呃,”魏中书迟疑了会儿,道:“皇上,老臣有一个法子,不知当不当讲。”
“什么法子?快说!”
魏中书道:“如今李尚书才带兵而回,尚未抵京,当初威慑狄人的那一场大战就是李尚书指挥的,狄人见了他便天然的害怕,如今危难之时,若顺势调李大人过去,老臣觉着或许是对症下药,也会比调别人过去更快奏效。”
“让李衾去?”李持酒沉吟。
正在此刻,有小太监过来:“皇上,太后娘娘有一句话。”
李持酒闻言,便先往内走去,谁知才到内殿,就给高公公迎着,高太监看看外头,小声说:“皇上,魏中书的意见可行。”
“怎么说?”李持酒问。
高太监道:“之前常有李大人有不臣之心的传闻,如今皇上下旨调他过去,他若听命立刻转道,足见一心为国并无反意,若他执意进京,那……”
先前李衾回京闹得沸沸扬扬,一些不明真相的朝臣甚为担忧,纷纷谏言,有的说该派钦差质询李衾,有的说该发兵阻止他,李持酒却并未轻信传闻,坚持按兵不动。
既然皇帝一言九鼎,群臣才勉强稳住,故而竟也朝野无事。
这会儿听高太监提议,李持酒想了想,道:“就算真的要调他去,朕也不想用这种法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要真的有谋逆之心,就算听命去了北关,以后依旧会反。何况朕也不想这么试探人心。他在南边的事情办得非常利落,又是这大半年不在京内了,就算是拉磨的驴也该喘口气,何况是李大人。”
高公公听他的比喻粗俗不堪,不知该哭该笑。
可看着李持酒毅然的表情,又细细想了想他方才这番话,却肃然道:“皇上所言很是,是老奴多嘴了。”
李持酒却抚了抚下颌,道:“高公公,我想出宫一趟。你帮我在太后面前打打掩护。”
高太监道:“皇上出宫?要去何处?”
“呃……”李持酒想现编个借口,一时找不到,就笑道:“总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放心,绝不胡闹。”
第112章
魏中书跟兵部左侍郎离开武德殿的时候,天上的雪还在绵绵下着。
侍从高高地撑着伞,两人走了片刻,魏中书说道:“皇上虽然玩心仍盛,但这段日子倒还算安稳,原本之前还担心到底是有些为难,不料还是萧尚书说的对,到底是个可造之材。”
左侍郎道:“说来下官也曾捏了把汗,当时我们李尚书回京路上,御史们吵吵嚷嚷说了那么多危言耸听的话,我还担心皇上也按捺不住会发兵引动干戈呢。”
魏中书笑道:“我却也有些猜不准皇上的心了,本来我也担心他年少气盛,且之前不管是传闻里还是所见所感,都是个颇为激烈的人,还以为定要蛮干起来呢,没想到竟很沉得住气。”
左侍郎却又叹了声,肩头一沉道:“好歹尚书大人要回来了,这兵部少了他总觉着没了精神气儿。只如今北关的事情尚且不知如何解决,皇上怎么也不下决断?还是说要等着我们大人回来后再做分派?那边的战事可是贻误不得啊。”
魏中书想了一想,道:“这个倒不必太过忧虑,咱们这位皇上也是军中出身的,战情如何他心里最清楚,必然会有主张的。”
两个人说了几句,看宫内的太监们正忙着打扫地上的雪,魏中书环顾周遭,却又笑道:“原先还说干旱,这雪倒是来的及时,可见皇上是个有福气的人啊。”
半个时辰后,李持酒换了一身玉色的袍子,外头披着松花缎的狐裘大氅,只带了乘云跟两个侍卫,出了午门,上了马沿着御街往前去了。
自打登基,李持酒一直都在宫中,从未外出过,这还是头一遭。
因为下雪的缘故,路上的行人很少,马儿过了御街,在街巷里拐了几回,才停在一所宅子跟前。
这房子的大门紧闭,门口上的雪并未打扫,李持酒在马上打量着面前的门头,明锐的双眼里透出了几分清冷。
身后的乘云慢了一步,追过街的时候心里就止不住诧异了,此刻见李持酒在门口停下,他便早早地从马上滚落下地,跑上前来有些惶恐地唤道:“皇上……”
李持酒回过神来,淡淡的吩咐:“去开门。”
乘云呆了呆,忙答应了声赶去敲门,敲了半天里头才有个苍老的声音道:“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