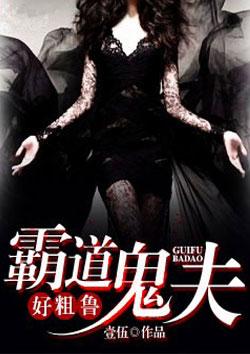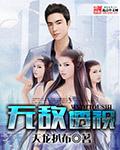趣书网>英雄吁天录 > 第一百八十一章 天牢之中内功相授汉人之中义气千秋(第1页)
第一百八十一章 天牢之中内功相授汉人之中义气千秋(第1页)
和硕亲王见这袁承天衣衫尽皆破烂,心中不知为何有股莫名的伤感,也许是见他现下这种困厄的情形有感而发吧!
袁承天也不再说话。和硕亲王也素闻这位袁门少主秉承其先祖袁督师的遗志,——反清复明,而且性格倔强,认为对的事情从来都是义无反顾,总是内心透着义气千秋,肝胆昆仑,是人所不及也。今次见他心意已坚,自己再多的话只怕他也未必听得进去,所以便不再说话,起身而去。
牢房又恢复平静,两个狱卒有一搭没一搭说起了京城的闲事。不由而然说到了额驸海查布被和硕亲王砍下一臂,皆因他在外面做下了荒唐之事,对不起清心格格。他们同时不约而同又看了看牢中的袁承天,不怀好意嗤嗤笑说什么,自然是说皆因清心格格牵挂于他,所以这位额驸便有些发狂,所以醉后做出不智的事来,似乎也是情有可原。
他又面壁思过,静下心来,可是又一时静不下心来,心想:不知大师兄可受到恭慈太后的惩罚——因为嘉庆皇帝已然答应自己不予问责,所以他不会出尔反尔,可是这位恭慈太后可是有手段的人,对她认为的乱党从不姑息,所以袁承天心中不免隐忧,可是自己身在牢中又无分身之能,所以也只有听天由命,想来掌门大师兄也不会有危险——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而且相貌俊逸招人喜欢,否则多铎亲王也不会委以重任,至于恭慈太后想来也不会十分为难于他的。
便在这时他隐隐听到墙壁声响,不是很大,但是清晰可闻,心下不由一动,心想隔壁牢房之中不知又关押着什么人?忽然墙壁上的一块石砖竟松动了一下,接着扑地被人扑落,便可见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袁承天不由惊了一下,倒退了几步。那人便笑了起来,说道:“原来袁门少主也是这样胆小怕事?”袁承天这才透过这窟窿可见一位头发蓬松的老人,只是经年不洗所以虱子乱跳,而且手背和脸上都显得格外肮脏,但是他神情却好,而且显得无所谓的超然的神态,似乎对这牢狱之灾无感,心下不觉起了好奇之心。
这蓬头老人见袁承天惊奇的样子,也不以为意,笑道:“小娃娃”他忽然住口,用手拍拍自己的脑袋呲牙笑道:“我怎么又犯了老毛病,总喜欢倚老卖老,为老不尊起来了。”袁承天见他形容虽不修边幅,甚为遢邋,心想他一定是在这牢房之中关的久了,神志不清,难免会胡言乱语,却也作不得真!
这蓬头老人见袁承天对自己的说话不理不睬,便自顾自道:“你是袁门少主——你的先祖可是我汉人之中的大英雄!只是可惜生不逢世,如果在下早生百多年定当助这袁督师一臂之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国!”他说话的口气极大,似乎认为自己也是当世之英雄,心想以他之现在情形似乎不可能,未免狂妄自大之嫌。这老人见袁承天似有不信的样子,于是搬着自己的手指,数了又数,忽然哈哈笑道:“我老人家已然被关在这里十年有余,只是他们并不杀我,偏偏关押着,还供养我老人家,怕我一时半刻死了?小兄弟,你说怪怪?”他忽然改口称表承天为小兄弟而不是娃娃,大约是觉得称袁督师后人不妥,便自改口称为小兄弟。袁承天倒不以为意,因为看他性情率直,不是那种表里不一,犯奸作科之徒,所以反而对他起了好感。
他一时说的性起,竟伸手又取下一块百斤重的大石砖,在他手中轻若无物,可见他可不是泛泛人物,似乎是曾经一位惊世骇俗的武林前辈。袁承天见他轻轻将石砖放下,怕惊动外面的狱卒。
袁承天这才注意到原来他早己将这石砖卸下又自填上,因为牢房之中光线黯然所以才不被人发现,倒不是他一掌可以推脱的。当这蓬头老人出现在这袁承天面前之时,这才看清楚他的真实面目,只见一条长长的刀疤自左额至右嘴角,赫然在现,仿佛一只蜿蜒的蚯蚓,着实让人骇然,然而他的眸子却是明亮,闪着光芒。袁承天便问他缘何被朝廷关押在此之时,这人显出沧桑,长长地叹了口气,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原来这人是为首辅,当事之时那多铎便瞧他不顺,因为一则他是汉人、二则身居首辅高位、三则他劝谏嘉庆皇帝优待,且对天下反清复明的帮派要循序渐进,以招揽为主,不可轻事杀戮,以缓解天下汉人反清复明的决心,但是多铎亲王却认为他这是姑息养奸,将来必成后患,所以便挟迫皇帝给他定了个里通外乱,意存祸乱朝党之罪,押入天牢,本拟再行择日在北京菜市口问刑;可是嘉庆皇帝念及他是先皇股肱之臣,所以便将他保了下来,只是死罪可赦,活罪不免,便自关押在这天牢之中。以后朝廷之事接踵而来,众人便将这位关押在天牢中的朝廷重臣给全然忘却了。
他见袁承天少年英气,而且有浩然之气,眉宇之间透着峥嵘,又且是袁门少主——袁督师后人;当然这些话都是狱卒平日里闲说的,所以他虽在大牢,对江湖之中的事还是熟稔于心的,所以今日一见这袁承天甚为赞赏,心底里不由想道:天下有他,自然汉人河山有重回之时!袁承天听他说完话,一揖到地,拜他昔年的义举,因为他若然力谏皇帝诛杀袁门弟子,只怕袁门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当时之事自己还未出任袁门少主,那时袁门还是赵三槐和沈冲为首一力支撑袁门,因为群龙无首,所以他们便迫切要找到袁门少主,机缘巧合之下让他们遇到,袁门的势力才有所改观,否则似乎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如果朝廷一心要剿灭,只怕也是旦夕之间的事情;所以袁承天出于内心感激才拜谢这位仗义直义的老人。
他见袁承天一揖而下,忙用双手去托,口中说道:“小兄弟太谦了。我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出于本心,心性使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民族大义,至于袁督师一生的忠义千秋,直怕后来无人可追!今日得见袁兄弟仿佛又见那肝胆昆仑的当年袁督师!见你犹见他也不为憾事了!想我汉失天下百多年,多是离难忧愁,总在忧患之中,有时不知理想何在?这十年之中,我便心无旁骛,一心钻研武学,有时也读圣人之书。记得书中有句话说的最为中肯,那便是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只是天下鲜有皇帝可以做到?因为高处不胜寒,世人总有迷失本性的时候,有时在功利面前忘了初心,正所谓一入魔道,再难回首!我也概莫能外,古今同理!”
袁承天忽然想到一个人的名字,道:“你莫非便是那位敢于直言的于敏中于大人?”这蓬头老人呵呵笑道:“不是我却又是谁?只时当时奸人当道,忠义之人难以有所作为,反而蒙冤入狱,这大抵都是历来忠臣良将的宿命。”他长长叹息之中是无尽的伤悲——不是官职被禠而是眼见奸人当道又无能为力的叹息!
袁承天听他说话还不知道多铎已殁,否则他也不至于伤感连连。现在他依旧关押在这天牢之中,大约是皇帝和众大臣都忘记了天牢之中还关着这于敏中于大人!世事难料,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数,非人也所能改变,——便如这袁承天命格天煞孤星,一生孤苦,且又祸及周遭至亲之人!其命不可改变,只有在忧患之中觉醒,砥砺前行,谁教他是袁督师的后人,又且是袁门少主,他不努力谁努力?因为放眼天下江湖各大门派皆归附于朝廷,只有袁门还在反清复明,在世人眼中似乎不识时务,然则他却有不屈的意志,相信汉人虽也懦弱,终也复国!
袁承天问他为何不出去,因为他既然有这武功,其实可以轻而易举出去,那些狱卒和巡视官兵等同无物!于敏中见袁承天说得真切,便笑道:“我在狱中有吃有喝,又何必去外面多生事非!”袁承天却道你难道不关心这汉人的天下。于敏中又自摇摇头,说谁做皇帝都一般,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于天授所命那也就罢了,只不过是虚枉之词,因为将相王侯,宁有种乎?他也不愿再见世上那些龌龌龊龊之事,倒不如在这狱中清闲,偶尔可以翻看史书,以为借鉴。
袁承天见他神色肃然,说的郑重其事,心想也是,世上之人,人心险恶,有时为了功利爹娘和兄弟都可杀!于敏中不由又说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发生在康熙时的《明史辑略》案。这《明史辑略》是渐江南浔乌程人庄廷龙所写。这庄廷龙自小家境优渥,自小为贡生而入国子监,后来犯风疾双目失明,可是他喜读史书,决定辑录一部《明史》,于是集合门客众力所为,只是纰露出在史书中的年号,都写着明朝的皇帝年号,而不书满清帝号,以致为后来的小人吴之荣告发,于是朝廷震怒,缇骑四出,罹祸者七十余人,死者剖棺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子儿女极边苦寒之地充军为奴,一时天色变了颜色,是为有清一代文字大狱,一时之间,天下文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说是人人自危!清廷以为可以禁锢百姓思想,让他们不敢再提“反清复明”之事;只是他们焉小瞧天下千千万万有志气的志士仁人,他们心怀故国大明,虽一时蜇伏,未必无功,暗中私下依旧联络各方英雄好汉,共襄义举。
这件明史之案袁承天在昆仑派习武之时也听师父赵相承说过。记得师父神色凝重,直看南方,心中藏着无限心事,也是他是怀念故国明月抑或忍看大好河山沦为腥膻,自是意难平!当时袁承天听师父说到血脉贲张之时,也是心中不平,因为他见过世上太的不公的事,以强凌弱,处处可见,若想讨回公道只有以命相拼,因为世上别人不会为你出头,现在已不是先前那种情形了,处处透着可悲,人人自私自利,少有急公好义之人,因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于敏中见袁承天眼眸之中透着愤怒,他又轻轻摇头,不无感慨道:“而今是满清的天下,我汉人只有委屈求全,这样才能活命。袁兄弟这里有一密道,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出去!”袁承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这牢房的左侧有几块大石砖有松动的痕迹,心中便明白于敏中要自己逃出生天。他也只有苦笑摇摇头,心想我若出去必定从这天牢大门光明正大出去,而不是偷偷摸摸形同做贼,所以他婉言拒绝。
于敏中见他决绝的样子,不由说道:“好,有袁督师的风骨。我于敏中果然没有看错人。看来汉人有望,全靠你袁门一力支撑,至于我么,全作身在曹营心在汉吧!”袁承天见时日不早,便又打息运功。于敏中也不再留,便起身又从这石墙上的洞穿了过去。
一夜相安无事。袁承天在狱中一晃几日过去。这日听到外面喧鼓锣天,吵闹的一发不可收拾,心下奇怪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好那狱卒闲来无事便绪绪叨叨说起京城新近的事。原来这日是多铎亲王下葬之日,虽然他生前多行不义,而且心怀忤逆篡位之心,本应死后褫夺生前的一切爵位,然而念及皇叔的身份便不能过为己甚,还要顾及皇家颜面,所以经恭慈太后议定,还要风光大葬以示皇家的威严。至于世子多福安因为半癫不疯不于追究罪责,任由居住王府。这也是嘉庆皇帝念及儿时伙伴所以格外开恩,否则可难说了。
又过几日,忽然天牢中的狱卒个个神情紧张,似乎面对大敌,人人自危也不为过。袁承天觉得奇怪,难道宫掖生变,但是想想也不能,因为摄政王多铎已除,大内似乎已无大害,既使有也不至于人人惊慌,因为京城防守历来严密,因为京畿之地岂容他人侵犯?
晚间于敏中又取下那块石砖,探身进来,神神秘秘地说起另一间石牢中被囚的女子——似乎是江湖上什么越女剑派的掌门钟神秀,已有时日!袁承天心中一动,原来这位钟掌门还被关押在此天牢,只是惊奇之余又是悲伤,心想钟掌门虽为女子却不让须眉,自己如若能脱困可要救她脱却牢笼,否则枉为侠义!袁承天说起这牢中狱卒的异样之时,于敏中哈哈笑了起来,说道:“你休看他们平日威风凛凛,实则都是虚有其表,虚张声势,一旦外面有风吹草动,他们便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生怕出了意外,他们可担不起这责任——须知这天牢之中押着的尽多是十恶不赦之人,当然这是朝廷的说法,因为在皇帝眼中胆敢忤逆犯上的人都是十恶不赦之徒。袁兄弟江湖险恶,人心如蛊,其实朝堂更甚于则,时时倾扎,所以我觉得待在这挺好,可以好好潜下心来,心无杂念,好好习练武功,不强似他们一帮人乱哄哄在哪里争名夺利?”袁承天听他说这番话也不无道理,心想:有时无名无利,和光同尘却是好,可是人人安于现状,那么这天下永远是满清的,汉人只有在他们制下无功。
忽外从外面涌进许多侍卫,护送和硕亲王舒尔哈齐走进,只见他神情肃然,气氛有些压抑。他先令人打开袁承天的牢房向里面看了看,只见袁承天闭目静坐,仿佛嗒然若丧——适才的响动早已惊动了他和于敏中。于敏中见势不对,又慌忙回到自己牢房。袁承天又将石砖填入用乱草胡乱遮挡不被人发觉,刚刚就绪,便听到脚步声到了牢门之外,他便不加索地打地静坐,对和硕亲王他们这干无视,这样才可打消他们的疑虑!
和硕亲王见袁承天所处的牢房没有异样,这才稍为放下心来,向一人说道:“傅提督太后不念旧恶,只许人才,十分看重于你,以往之事过往不咎,今日擢任九门提督,京城防卫一切事务你可要用心,因为新近传言袁”他说到此处似乎觉察自己说漏嘴,透了机密,便住口不言,回身让狱卒关上石牢的门,然后对傅传书道:“提督大人,你可要十分小心在意,因为王府侍卫侦得袁门四大堂主要进京解救他们的少主,也便是你的师弟袁承天:你可要加强防范,千万不可有了纰漏,因为目下的袁门已不是以前的乌合之众,而今已是势力大炽,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皆有其分舵,门人弟子三十万之众,而且秉承当年袁督师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枉想重复朱明天下,可不是异想天开,想我满汉八旗子弟精锐尽出,立刻让他们形销影散,灰飞烟灭!”其实他说这话不尽不实,因为现下的军营兵士可说已不复当年之勇,且又久享太平,军心涣散,可说是武功废驰,那还有当年满洲八旗之骁勇,承平岁月早已磨销了他们的勇气,如然真得和袁门弟子较量,未必有胜算的机会,甚而一败涂地,因为袁门弟子知道他们身处逆境,不进则退,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如此;所以砥砺前行,总是心怀忧患,知道肩上之责,不是为了一个袁门,是为了心中理想,天下的千千万万的生民,所以才感到人人自危,不可懈怠于世局。
傅传书心中自然知道这位和硕亲王言过其实。原本这也怪不得他,因为他少在江湖走动,根本不了解江湖上真实的情况,依旧活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之中,所以难免偏失,他身为标下也不能尽实而言,只有虚以委蛇,敷衍了事,因为你若直言只怕又犯了王爷的忌讳,徒惹人家不高兴,何苦自讨没趣,这些浅显的道理傅传书岂有不懂的道理?如若耿直行事,无所讳言,只怕又是第二个袁督师,他自然不会做这无功的事情。
他们自以为牢中的袁承天并未听到他们的说话,但是他们怎知袁承天屏息内息,将他们的说话听得一清二楚,心中不禁又惊又喜,惊者乃是掌门大师兄傅传书非但未受重责,反而被朝廷擢升九门提督,看来大师兄非但没有丝毫悔过,反而要为朝廷效力,真是昆仑派蒙羞,如果已去的师父有知不知该当如何后悔当年收留他在昆仑,本来寄于厚望,光大昆仑一派,谁想他却私心过重,忘了本来面目,真是无可救药!喜者乃是袁门四大堂主要来营救自己这个袁门少主,这样也可以不违誓言挣扎囚笼,解救钟掌门一并出走,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他便在石床之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到中夜他也不能入寐,因为心中有事。
忽然墙上石砖又被那于敏中取下,又窜身过来,看着袁承天忧愁善感的样子,摇头笑道:“真像,真像”他自说自话又道:“少年人忧患总是有的,像极了少年时的我”他太息看了看石牢四壁冰冷,但是却阻止不了虫蚁的爬动——它们也是为了生存而不得闲下来,可见世间万物生灵皆是不易!有时想到人生不过来来去去一晌空,又争什么名,斗什么利,不免心灰意冷;可是坚强如铁的总会在渺茫失望的黑暗中寻找点点星光,照亮前途的路,因为不弃所以成功,便如屈原大夫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生死一生不正诠释了生命之真谛,他的话语感醒世间多少迷茫不自觉醒的人,让他们明白此生来世上,你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也许:大义真当以死争!
于敏中双手簌簌扒动地上的茅草,堆在平地便自盘膝坐下,心有所感,言有所发,说道:“我少年之时也是心高气大,眼底无人,每与人论,也是壮志说天阔,怒指乾坤错!自以为天下英雄非我而何?可是后来踏入仕途才知差强人意,每每不如意,入了牢笼,不得施展!因为世事多变,非是人为,亦是天意。”袁承天见他说得悲凉,心有同感,想自己一生孤苦,虽然光明磊落,然而不会屈就,所以不受别人待见,人家以为他是个不通世务的小子,不会融会贯通,不会逢场作戏,一味耿直,仿佛浊世中的一股清流,可是却是处处有人作梗,发难于他,想让他就范;可是他不为所动,依旧坚守自己的信念,不随波逐流;这样一来反而又显得自己清高不入流,更加不受待见;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因为当年先祖袁督师也是如此一般不为世俗之人所理解,反而以为他里通鞑虏,卖国求荣;后来终于拔乱反正,只是却是满人的皇帝,可不是天大的讽刺!
于敏中见袁承天并不说话,然而看他面目表情便了然于胸——因为他多少也听闻过江湖上的事情——至于袁门天下人不知道的只怕很少;因为那可是朝廷眼中的忤逆乱党,是反清复明的中坚力量——因为昆仑派归顺朝廷,丐帮也见风使舵依服朝廷,以为为清廷效力,可以得到赏识,也不必如以前那样东躲西藏为朝廷有司衙门缉拿,现在可以安枕无忧,可说名利双收,可不胜似那袁门那样四下躲避,不为朝廷所容。只是这些江湖上这些所谓名门大派不过都是沽名钓誉之徒,只为眼前利益,却不知道民族大义,更加不知自己的本来面目和身份,怡怡然以为自己也是朝廷中人了,只是人家却未必这样认同,处处提防着他们,因为在人家的固有认知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可说是仰人鼻息,没有自尊,空有武功而无坚守正义的灵魂,真是枉为一代宗派!
于敏中道:“此生生在尘世间,不为功名不为钱!我欲乘风上云天,稽首谪仙不叩首!笑傲只为此生有,丹心偏在昆仑巅!吹发长嘘为何故?仙长练丹为何求!长生海外求丹药,不见当年秦始皇。袁少侠尊师当年在昆仑之巅,眼见天下生灵蒙难,而自己有志难伸,不觉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古风。尊师赵掌门一生令名出于尘表,侠义满天下,以济世救民为怀,从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天下每有瘟疫灾情便施丹药灵符,且又祭天告求上苍怜我世人,度此劫难!可以说江湖中如尊师这般济世爱民的江湖宗派万中无一!——因为世人都为市俗蒙蔽蛊惑,失去本心,人人都入魔道,而且不自知自省,反以为功!只是现在昆仑派日趋势微,只怕你的掌门大师兄难脱干系!”
袁承天道:“古之义侠都是排难解纷,义所当为之辈,那是现在都是斤斤计较得失,全然不把家国放在心上,便如我掌门大师兄而今依附朝廷,忘了我派宗旨反清复明!”于敏中对袁承天所说反清复明并不排斥——因为他也是汉人——知道虽然现在满人皇帝也任用汉人为官,只是处处都是提防,因为害怕他们起了异心,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从来都没有唯贤用人,因为害怕汉人起了贰心,危及社稷,所以都用人制衡,不让其权力过大,归根到底还是心存猜忌!
于敏中见这位袁门少主一幅忧国忧民的样子,说道:“我少年之时也如你一般,只是过来多经忧患,虽位列朝廷,然而却无法憾动乾坤,也只能尽力而为。袁少侠我见你面像清奇,骨髂定也不凡,不是寻常之人,心中定有经天纬地之能!”袁承天苦笑一下,说道:“我可比当年的袁督师差的远了!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而我却一事无成,碌碌无为,浑浑噩噩于世间,虽多方奔走,可是响应,却是无功!有时我便想索性放弃吧!与世浮沉——可是每当入寐之中便会见到已殁的爹娘声声斥责我为袁门不肖子孙,——如果一个人死且不惧,世间又有何事不可为?我想正是如此古往今来的大英雄才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家国至上吧!所以我又不能全然放弃抗争,因为我见天下之人皆在梦中,不知白昼黑夜,只怕唤也不醒,他们反而会认为我是个痴人,妄想逆天改命,究是不成!唉,于前辈你说我该当如何?有时我心乱得很,仿佛一团乱麻,没有头绪”
于敏中见他忧患意识之中又有十分的坚强,心想:他终究不是懦弱之人,毕竟有袁督师的血脉!自己而今已经看破世俗,又有何留恋,不如将自己在这牢中十年苦练的内功心法悉数传于这位袁少侠,让他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为他见袁承天语出真诚,决非作伪,不是奸邪小人,将来可堪大任;所以他便将自己的想法说来。
袁承天无功受禄,坚辞不就。于敏中哈哈一笑:“老夫已是残年之躯,纵然有朝一日出去,也是无用,倒不如将这些年的内功心法悉数相授——因为袁少侠你年青有为,心有浩然之气,胸中俯列乾坤,将来这天下还要你们年青人去争所以”袁承天不待他说下去,便执手相拒说道:“不可以!于前辈这样一来于你身体有莫大的损害。我决不接受!”因为他知道这于敏中若将自己的内功心法传授于己,那么他便元神大伤,只怕命不久矣,因为他久在石牢之内,难以呼息外面的新鲜空气,全倚仗着体内的这股内功心法支撑运行周身经脉,否则换做旁人只怕早已发狂而死了;好在这位于敏中大人非是寻常之人,少年之时竟在武当习武,所以心静如水,耽于寂寞,不为外物所扰,所以竟可练成内功心法,其实不外乎源于武当道家内功,其实与昆仑派的“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的内功心法殊途同归;所以他今日才有意将这内功传于袁承天,期于后望。只是袁承天不明就里,害怕这于敏中一旦武功相授,体内的元神不免受损,那么有可能危及于性命,所以才坚辞不就,可是于敏中却不这样想,因为他觉得已是风中残年,自己心中的理想只有让这袁少侠去实现!人生不过是悠悠一场大梦,来日无多,去日已到;他便心无所恋,所以便无所挂念,心想这袁少侠一身肝胆,可比昆仑,将来定有一番作为,自己纵死也是无所遗憾——只因他心中依旧有汉人天下的家国梦!
袁承天见他决绝的样子,心想如果自己再一味相拒,反而显得虚伪了,所以也就欣然受之。
石牢之内此时本是万籁无声,不意忽然竟有只饿得发狂的的耗子窜出,来到放青菜和馒头的石桌之上,竟不畏人自顾吃起来。袁承天竟视而不见。这于敏中也不伤害于它,两个人似乎心有同契,对它视如不一。其实不是他们两个人没有看到,只是不想出手伤害于它——毕竟万物皆有生灵,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亦或身后还有小耗子在等它们回去饲食,所以众生皆是平等,无所谓贵贱,只是世上有人却不这样想,反而噬杀成性,所以到头来多行不义必自毙,结实是落了个悲惨的下场,只是后世之人从来不吸取教训,反而来回重复这悲剧,——是人为?是天意?皆是不可知!
待得半个时辰,于敏中额头汗水滴下,头顶发际也是氤氲气散,向石牢上面飘散。他拍了拍手,轻嘘一口气,说道:“今日终于得偿心愿,也不枉在这世上走一遭!”他话中之意自是说今日武功相授,心中宿愿已了,余生再无遗感,虽不可见收复天下,但是终究是有了希望!袁承天体内此时但觉轻盈,因为蓦然之间多了别人十年的功力自然非同寻常,只是自己受益,而于敏中前辈身体受损心中总觉得愧疚过意不去!于敏中却坦然一笑,说道:“侠义之人正当排难解纷,义所当为,那有什么斤斤计较?袁少使怎么于小节之处这样放不下心来,这也大大不对了!英雄好汉应该去为心中理想去挣,而不是一味妥协,那样岂不是成了无用之材?”
一番话如醍醐。灌顶的话语顿时开悟,心想自己总是优柔寡断,遇事不决,所以遗失战绩,总是被人算计,是自己心肠不够狠,还是太过悲天悯人?一时忧愁难当。于敏中忽然悠悠念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也,实乃天授!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袁承天听他将这话说完,心中为之一动,因为这是洪武大帝朱重八讨蒙元之檄文,可见句句在理,字字有万钧雷霆之力,可以昭告日月,明白无误告戒世人我汉人不懦弱,有时积弱只是一时,终将会将夷狄驱除中土,恢复中华!由此可见这朱重八虽出身低贱,身世并不显赫,少小之时便久经忧患,知道世上百姓的疾苦,所以当他君临天下之时便严惩贪官酷吏,因为他对百姓的苦难身同感受!
于敏中道:“袁少侠大约你也知道这是洪武大帝朱重八讨蒙元之檄文,可说气势千钧。文中的意思大约你也明白不过,自当砥砺前行,想当年他出身不可谓不惨,上天从来没有怜悯过他,可是他却从不妥协,在忧患罹难之中前行,在刀枪火雨中磨练心志,可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可成大事也!所以你怎么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怨天由人,焉也不是!”他还有下一句话只是没有说出来,那便是:你一点也不像袁督师的后人!
袁承天知道自己以后行事再也不可以优柔寡断,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因为目下皇帝已被恭慈太后挟持——虽然是母子,可是行为作风却是截然不同:恭慈太后的眼中凡是反清复明之辈一律杀无赦,不问情由,因为她担心对汉人的宽容会带来他们肆无忌惮反抗朝廷,得不偿失,索性便行肃杀政策,以儆效尤,让他们人人自危,都噤若寒蝉,那么他们的忤逆想法就会打消,只是这只是恭慈太后一厢情愿的想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她不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积萤之下,可以成光的道理!尤以袁门为最,这百多年间起起落落,沉伏之间,虽有时似乎要亡但是总会留下薪火相传,绵绵不绝;便似袁督师的遗志看似中断,完则暗中依旧不畏朝廷缇骑四下揖拿乱党,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放弃,那么这天下永远是满人的,汉人真的要无缘了,所以前赴后继,循循不绝,因为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向来是天下有志之士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