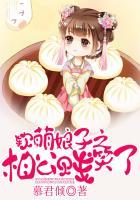趣书网>云麓词心录:白云着 > 第270章 墨痕与星子落满襟(第2页)
第270章 墨痕与星子落满襟(第2页)
“冻云垂野朔风号,独向寒林拾碎瑶。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枝瘦犹存清骨在,雪残偏带墨痕凋。
镜头凝住三冬韵,光影洇开半阙箫。
忽忆那年山径冷,君呵冻指护冰绡。”
案头的宫灯忽然爆出灯花,火星溅在《碎光集》手稿上,将“光影是时间的琥珀”这句映得忽明忽暗。沈砚生起身去调灯芯,煜明趁机翻开相盒最后一格——里面竟不是照片,而是张泛黄的电影票根,日期是七年前的平安夜,《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末场。
“那天散场时下雪了,”沈砚生的声音从灯影里传来,“你说电影里的对称构图像宋词的平仄,我却觉得,雪落时你睫毛上的光,比任何镜头都温柔。”煜明捏着票根的手指微微发颤,想起那晚他们踩着雪走回书院,沈砚生忽然举起相机,说要拍“两个影子的对仗”。后来那张照片里,他们的影子在路灯下交叠成枝桠的形状,像谁在雪地上拓下的半阙《踏莎行》。
【第三章词心与光影同辉】
雨停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沈砚生将最后一帧照片嵌入影集,那是张云麓山的全景——晨曦从云海中破出,将连绵的峰峦染成金红,山坳里几户人家的炊烟,正与云雾缠绵成水墨长卷。
“这是你去年生日那天拍的,”煜明的声音里带着睡意,“你说要捕到‘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光,结果在山顶冻得直打喷嚏。”沈砚生合上影集,指尖在封面刻着的“碎光”二字上停留许久:“其实那天最妙的,是你递来的暖手炉,炉盖上的缠枝纹,恰好投在取景器里,像给朝阳镶了道金边。”
书案上不知何时多了叠信笺,最上面是煜明昨夜写的《碎光集·序》手稿:“砚生之镜,非独捕光,实乃织梦。其于晨昏晦明间拾得的碎光,皆为岁月缝在光阴里的金线。而吾与砚生,恰是执镜与握笔之人,以光影为墨,以词心为绢,共绘这云麓山的万千气象……”
窗外传来第一声鸟鸣,惊散了檐角的残雨。沈砚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个锦盒,里面是枚老式莱卡镜头,镜筒上刻着细密的缠枝莲纹。“这是我祖父留下的,”他将镜头递给煜明,“当年他说,好镜头要懂得‘留白’,就像填词要懂‘空际转身’。”
煜明接过镜头,对着初升的朝阳。光线穿过镜片时,在他掌心投下细碎的光斑,像谁撒落的一把星子。他忽然想起七年前在暗房,沈砚生第一次让他看显影液里浮起的影像时,那双眼睛比相纸上的银盐还要明亮:“你看,光会写诗。”
此刻,云麓山的晨雾正顺着窗棂漫进来,将案头的《碎光集》影集染得半透明。煜明提笔在序言末尾补上最后一句:“盖因友情如光,照见彼此词心,方使这碎光成集,墨痕生暖。”沈砚生凑过来看,鬓角的碎发扫过煜明的手背,忽然低笑:“这句倒像晏几道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只是我们照的,是镜头里的万千光阴。”
【诗词嵌章·鹧鸪天·题《碎光集》终卷】
“云麓山横水墨屏,镜头收尽古今星。
砚池冻墨融春雪,词稿飞香绕画棂。
拾碎光,织银屏,七年光影入青绫。
他年若问相逢处,一片冰心在镜铭。”
当第一缕朝阳越过云麓山顶时,煜明发现影集最后一页夹着张新洗的照片。画面里,他与沈砚生并肩站在银杏树下,各自捧着相机与诗卷,阳光透过叶隙在他们肩头织出金色的格子,像谁用光影谱就的《相见欢》。照片角落有沈砚生的题字:“与煜明兄同观碎光,觉岁月如镜,照见词心。”
博古架上的糖炒栗子早已凉透,却仍散着淡淡的甜香。煜明望着窗外渐渐清晰的云麓山轮廓,忽然明白沈砚生为何总说“光要养”——原来那些被镜头捕捉的碎光,早已在友情的温养中,酿成了岁月里最温润的词章。而他们的故事,恰似这《碎光集》里的一帧影像,在光影与墨痕的交织间,永远停驻在云麓山最美的晨昏。
喜欢云麓词心录:白云着请大家收藏:()云麓词心录:白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