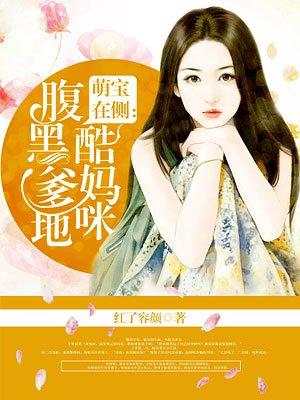趣书网>规则怪谈:她不是雨姐 > 第636章 修(第1页)
第636章 修(第1页)
顾十七站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册:“这是我最近的研习课题。”
张承接过笔记册,封面上写着《礼制革新论及其调和之道》。
“革新论?”张承抬头问。
“礼制革新,”顾十七重复道,“这已无需辩驳,成了既定之论。”
张承翻开笔记册,里面是更系统的思辨:
“依祖制,朝议本当代表最高权柄。朝议会对府衙应有监察之权。朝议会自身则当受士农工商各界的监督。
然现今朝堂之上,朝议不仅无权,其遴选亦脱离庶民。
朝议代表非由民选,而是由上官指派。
翰林院亦无参议政事之权,无力匡正政令之失。
反成了勋爵休养的清闲之地,空有虚衔而无实权。
此皆礼制革新之实证。当今之制实为特色革新之道,早已不是隐秘。
说明已放弃庶民之本。如今所求不过是保全统治权柄,玩弄阶层调和,弃了根本之道。
实为天下权贵联合,共压庶民。”
张承合上册子,手微颤:“十七哥,这些见解从何而来?你不惧…”
“何惧之有?”顾十七轻笑,“我一介市井摊贩,能有何牵扯?何况这只是清谈思辨。”
他取回册子,轻抚封面:“我所思惟在调和之道。真正的共治应为:朝议挥实权,若宰辅偏离庶民立场,朝议有权推举心系百姓之人上位。
翰林院能纠偏政令之失。换言之,国家最高权柄当在朝议与翰林院手中,如此方能称共治。若权柄不在此二者,便是礼制革新。”
张承沉默良久,终问:“那你为何择此营生?以你才学,本可…”
“可入仕途?”顾十七摇头笑道,“那岂非成了自己最厌弃之人?宁在街角摆摊,保全思辨之自由。”
他指窗外繁华街市:“你看那万家灯火,璀璨如画。可知光华背后是多少百姓血汗?将来只怕连奉献血汗的资格都将失去。”
“三邦之喻可曾听过?”顾十七忽问。
张承摇头。
“齐若将财帛尽分贫民,
楚视贫民如草芥,转投谋士贤才,
燕则不事生产,一味模仿齐楚。
结果楚邦技器精进,反身吞并齐邦。
燕邦兼采二者,却集其短而非取其长。
技器不兴,民不富足。
名义承齐统,实为楚之傀儡。
这般兼收并蓄之制,你可觉先进?我只见四不像之弊。”
顾十七转身直视张承:“为何不分你羹食?藩王不愿与你同享。宁灭你,不分你。”
张承只觉晕眩,原为家常烦恼而来,不意听得这般惊世之论。
“当…如何是好?”他声若游丝。
顾十七拍拍他肩:“莫绝望。认清世相乃改变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