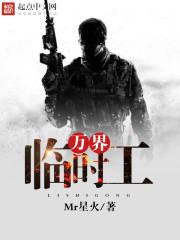趣书网>我来现代当明星 > 第49章 文明课程进校园(第1页)
第49章 文明课程进校园(第1页)
教育部那纸批文下来的时候,苏明远正站在明远书院二楼的窗前。细雨如丝,落在院中那棵已有三百年树龄的银杏上,叶片沙沙作响,仿佛无数先贤在低语。他下意识地捋了捋根本不存在的长须——这个习惯从他穿越到现代后仍改不掉,每当思虑重重时,右手总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
“苏院长,各部门负责人都到齐了。”助理小陈轻声提醒。
苏明远转身,青石板地面映出他修长的身影。三年了,他依然不习惯这种被称为“西装”的现代服饰,总觉得宽袍大袖才符合读书人的体统。但既然来到了这个时代,便要入乡随俗,正如他在大明万历年间高中状元时,也要学习官场礼仪一般。
会议室里,他望着那些期待的面孔,清了清嗓子:“诸君,”刚开口又自觉太过文绉,改口道:“各位同仁,《文明通识课》即将进入全国中小学,这是我们明远书院成立以来的最大使命。”
投影仪上显示出教材封面——淡雅的宣纸底色上,一枚殷商云雷纹环绕着现代二维码,古今交融的设计让他这个穿越者看得心中微动。
“我们要教的不是死记硬背,”苏明远继续说道,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而是要让孩子在经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明坐标。”
话说出口,他自己先怔了一瞬。这不正是他穿越三年来最深的感悟吗?从大明万历三十五年的状元郎,到如今现代书院的院长,他何尝不是在寻找自己的文明坐标?
教材推广出奇地顺利。最让苏明远意外的是,北京某中学的历史老师赵海平居然用如此生动的方式讲授“古人的智慧”单元。
那天他悄悄坐在教室后排,看赵老师举着手机比喻飞鸽传书。阳光透过宽大的窗户洒在课桌上,空气中浮动着细微的粉尘,仿佛时光的碎屑在光束中舞蹈。
“现在,请用文言文给父母写条微信。”赵老师话音未落,教室里已经响起一片兴奋的窃窃私语。
苏明远忍不住微笑。他想起了自己当年第一次给远在家乡的母亲写信报喜中的情形,那小心翼翼蘸墨落笔的紧张,与眼前孩子们兴奋地戳着手机屏幕的神情,何其相似。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最先举起手:“老师,写好了!‘母上大人,今日月考得甲,晚餐欲食东坡肉,望准奏’。”
全班哄笑,苏明远却忽然有些恍惚。笑声穿越四百余年,与他记忆中国子监同学们听到某位同窗家书内容时的笑声重叠在一起。人心相通,古今无二。
课后,赵老师认出了他,急忙迎上来:“苏院长,没想到您会来听课。”
“赵老师课上得精彩,”苏明远真诚地说,“尤其是‘见字如面’的心意不变那句,深得我心。”
赵海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教材太理想化,直到看见学生们的反应。特别是留守儿童小斌,”他指着后排一个正在整理书包的瘦弱男孩,“那孩子父母在外打工,学了‘今人的传承’单元后,居然用文言文给父母打电话。他妈妈说,这让她想起自己小时候”
苏明远望着那个男孩,忽然想起自己七岁开蒙那年,父亲赴京赶考前摸着他的头说:“远儿识字后,便可给为父写信了。”一别三年,当他终于能歪歪扭扭写下第一封家书时,母亲高兴得落了泪。原来跨越四百余年,笔墨传情的温暖依旧。
深秋时节,苏明远再次造访那所中学,正逢“礼仪实践课”在食堂进行。
食堂里飘着饭菜香气,学生们排着队,却与往常不同。取餐时,他们用公筷夹菜前总会向同学行一个简单的“叉手礼”——双手在胸前交叉示意,源自宋代的一种日常礼节。饭后,孩子们自觉收拾餐盘,模仿古礼中的“撤馔”仪式,将餐具整齐地放回指定区域。
“这是学生们自己发明的‘新食礼’,”校长自豪地介绍,“学了‘今人的传承’中关于传统饮食礼仪的部分后,他们就想出了这个结合古今的做法。”
苏明远站在门口,看着孩子们庄重又活泼地践行着自己设计的礼仪,忽然眼眶发热。这一幕何其熟悉,仿佛看见大明国子监的学子们餐前诵读《悯农诗》的情景。形式虽变,精神犹存。
“苏院长?”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转身,是那个叫小斌的留守儿童。
“学生有一物想赠予院长。”男孩双手奉上一本作文本。
苏明远接过,翻开到标记的那页,只见标题写着《给父亲母亲的书信》。文中最后一段让他心头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