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书网>田园女神的逆袭甜宠记 > 第363章 图纸交接启动计划(第1页)
第363章 图纸交接启动计划(第1页)
苏芸接过皮囊,转身离去的脚步轻而稳。我站在院门口,望着她背影融进晨雾,手中那份“新禾”代号的指令仿佛还在烫。柏舟站在我身后,没说话,只是将一盏油灯递到我手里。灯芯噼啪响了一声,火光映着他眼底的血丝——我们一夜未眠。
我低头看了看灯,又抬眼望向远处。东原的轮廓在薄光中若隐若现,像一张尚未落笔的纸,等着被填满。
当天午后,我在西仓房召开了第一场筹建会。工匠、协作网联络人、李商人,还有几位愿意出资的村民都来了。桌上摊着三张舆图,中间那张正是东原。我取出便携采样仪,将昨日上传的土壤数据投影在墙上:氮磷钾含量、ph值、微生物活性,一条条曲线清晰排列。
“东原可耕,五十亩起,三年扩至三百。”我说。
话音刚落,就有工匠皱眉:“五十亩说小不小,可人手呢?咱们这边技工刚派出去几个,再抽调,田里谁管?”
李商人捻着胡须,缓缓开口:“人是难处,但更难的是钱。建渠、整地、搭棚、买种,哪样不要银子?云娘子,你心里可有数?”
我点头,从袖中取出一份账册副本,推到桌中央。
“基建预备金已锁定,下一批灵菌干利润四成归入。李叔这边预付的定金,加上几位乡亲的合股,目前可动用资金共一千二百两。期投入八百,余下四百作应急储备。”
众人低头翻看账册,有人轻声念出:“水源取荒渠,避官田,不占民宅……连合规都写进去了?”
“是。”我答,“咱们要走得远,就得走得稳。”
屋内静了片刻,随后一位老工匠抬手:“我愿投一百两。但我有个条件——新基地的灌溉图,得由我来画。”
我愣了一下。
他咧嘴笑了:“我年轻时在府城工坊干过两年,后来回村种地,手艺没丢。昨儿听柏舟兄弟讲那‘梯度排水法’,我心里早画了几道线。若你们信得过,我愿把图纸交出来,也把经验带上。”
我当即起身,向他拱手:“若您肯牵头,那是我们求之不得。”
他摆摆手,又道:“不过图纸不是白给。我只提一句——等基地建起来,我想让徒弟来试试手。那孩子脑子活,前些日子还琢磨着把脚踏水车改出个省力机关。”
我记下,郑重道:“等土方动工,我亲自去请他。”
会议继续,资金交接在众人见证下完成。李商人将一只沉甸甸的木匣放在桌上,打开,是成锭的银子和几张银票。我当众清点,登记入册,每笔款项都注明来源与用途。最后,我拿出三份合作文书草案,分下去。
“这是初步拟定的合作条款。”我指着其中一条,“工匠按工分计酬,安全责任由管理方承担,但违规操作除外;投资人按投入比例分红,每季公开账目;所有建设进度,每月初在仓房公示。”
有人问:“若有人中途退出呢?”
“可转让份额,但须经多数股东同意。”我答,“新基地不是一人之业,是大家伙儿一起拼出来的路。”
讨论持续到傍晚,条款逐条敲定。有人坚持要加一条“技术保密”,我却摇头:“技术不藏私。但凡来学的,只要肯干,就教。可若拿去另立门户、损人利己,那便是背信,人人可究。”
最终,三份文书落笔签字,按上手印。红泥印在纸面绽开,像一簇簇新生的芽。
签约毕,李商人忽然从包袱里抽出一卷竹简:“这是我早年走南闯北时攒下的,几页关于暗渠引流的图样。原是备着防旱用的,一直没机会试。如今你们要建新田,或许用得上。”
我接过竹简,指尖抚过上面精细的刻线。一道道沟渠走向、落差设计、分流节点,竟与系统推演的最优路径有七分吻合。
“这图……”我抬头,“您愿授权我们使用?”
“用,当然用。”他笑,“但有个条件——等新渠通水那天,我要亲眼看着水从第一道闸门流进来。”
我郑重应下。
次日清晨,我在村中广场支起一张长桌,桌上摆着东原的舆图、土壤报告、合作文书副本,还有一小袋灵泉水稻的种子。村民们6续围拢过来,有人问:“云娘子,这是又要折腾啥?”
我拿起那袋种子,举高了些:“这不是普通的米。它长在咱们的地里,卖到镇上酒楼,能让掌勺的师傅说一句‘这饭香得不一样’。”
人群安静了一瞬。
“现在,我们要在东原,种出更多这样的米。”我继续道,“新基地建起来,需要人挖渠、整地、搭棚、管水。工分照计,报酬照。将来收成好了,入股的分红,不入股的也能优先雇用。”
一位老农拄着拐杖走出来,眯眼看着舆图:“东原那片地,我年轻时去过。荒是荒了些,可土是好土。早年村里也想开,结果才挖了三天,天降大雨,沟塌了,人也伤了,后来就没人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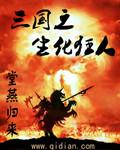
![道长先生[古穿今]](/img/16112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