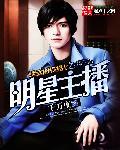趣书网>死亡实况代理人[无限流] > 第284章(第1页)
第284章(第1页)
闻言,岑昀几乎是一蹦而起,二话不说便将身后俩哥哥一并搂住了。
戚文二人还没和好,冷不丁被那么一抱,身子都贴到了一块儿去。俩人一时都乱了心神,表情皆有些不自然,那喜不自胜的岑昀却压根没发现。
薛无平眉开眼笑,合掌拍了几拍:“太好了!他爹他爷终于不用缠着我了!”
***
岑昀考得不错,最高兴的却是薛无平和方美。眼瞧着那两人兴高采烈地做了一桌好菜,赶忙招呼他们过来坐下。
那方美待人处事,是与薛无平如出一辙的豪横。饭菜快清盘的时候,他忽而兴高采烈地宣布一会儿整个铺子的人要一块出门散步去。
文侪一面把盘里的肉往岑昀碗里夹,一面诧异问:“去哪儿?”
薛无平咳了声,清干净嗓,说:“镇北那林子。”
文侪面上没什么变化,倒在心底暗自松了口气,眼下戚檐闷着声不肯说话,他也不肯服软,也就把刺立着,不搭理人。
他想着到宽阔的地儿走走,说不准心情就好了。
***
午后太阳也毒,幸而镇上多枝繁叶茂的大树,一路上走在树荫下,拂面的风既轻盈又凉爽,不带半点黏和烫。
岑昀在这铺子待了三年多了,早把镇子的路摸透,这会儿美滋滋地在前头领路,偶尔回头冲戚文俩人说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他全然不顾自个在其他人眼中,仅仅是在同空气说话。即便有时不慎对上那些个大爷大娘诧异的眼神,他依旧能送上粲然一笑。
文侪瞧着他,就像瞧着他和戚檐从前求而不得的自由模样。
他与戚檐那样的人,最不敢贪求的东西便是自由,家给他们的不是安巢,是锁链与重担,是责任和鞭策。
一句不能忘本便足够他们隐尽锋芒。
文侪抬手拨开那些拦路的枝条,指腹时不时擦过那些柔嫩的新叶,过分舒适的触觉叫他不由得蜷了指,只是那感觉又有丝异样的熟悉。
在哪里呢?
想着了。
是摸戚檐头发时常有的舒适感,那人的头发软,摸着舒服。
他想着想着,觉着自个儿正和戚檐吵架,总想他有些不好,便抱起那走累了的薛一百。
手不自觉地抚起它的毛发。
五人停在溪边,文侪正琢磨着放薛一百下来走走,忽而给身后伸出的一只大手惊了惊。
他回头正要骂,觑见的却是那戚檐。被叶片精心裁过的阳光浇在他面上,捯饬出分外漂亮的光影效果。
文侪知道,漂亮的不只是光影。
可他什么也没说,仅抿唇把头扭了回去。
身后很快传来戚檐那不夹一丝情绪的声音,他说:“你要一辈子和我这么闹着吗?”
文侪并不回答,仅蹲身将薛一百放下,反问他:“你呢?”
戚檐没有回答,所以文侪推开他自顾走了。
戚檐目送他走远,便愣愣蹲下来伸指去逗薛一百,起先嘴角还挂着笑,逗着逗着不仅吞了笑,就连脑袋也恹恹歪去了膝盖上。
他捡起根树枝在土地上画猫,虽说起先是要画薛一百的,可是后来思绪飞到九霄云外,到最后回过神时,他已在画旁标上了个“文侪”。
他自嘲似的笑起来,把那路过的薛无平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