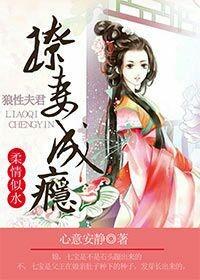趣书网>从俯卧撑开始肝经验 > 第360章 以暴制暴的意义美女老师的变化(第1页)
第360章 以暴制暴的意义美女老师的变化(第1页)
东都大学,法学院教程楼。
三楼的一间会议室内,气氛庄重而肃穆。
长条形的会议桌后,并排坐着三位考官。
两男一女,年纪约莫都有四十来岁。
其中一个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正是昨天笔试出现的那名监考老师。
他面前摆放的身份标识牌,写着名称“法学院教授罗洋”。
“方同学。”
左侧一位中年男性考官翻阅着手中的材料,抬头看向对面的年轻人,语气严肃地说道:
“我想问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案例,当事人因循法律途径维权无果,最终采取私刑,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寻求正义。”
“对于这种现象,如果当法律无法有效保护受害人时,你认为,我们应该支持这种私力救济吗?”
坐在他们对面的年轻考生,正是方诚。
他今天穿了一身得体的正装,纯白的衬衫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黑色的西裤衬得双腿愈发修长。
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让他的气质更加温文尔雅。
听到这个问题,方诚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不疾不徐地开口,声音清淅而沉稳:
“各位老师,这是一个涉及法律伦理与价值判断的深刻命题。”
“从法律人的立场出发,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正当防卫外,任何形式的私力救济都应当被严格规制,因为这会破坏法治的根基。”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现实中的一种困境。”
他一边从容讲述,一边与提问的考官保持着眼神交流,语气诚恳:
“法律对弱者的保护确实存在不足,司法资源的不均衡、诉讼成本的高昂、执行环节的乏力,这些都可能导致个体的正义诉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
“这种制度性的失灵,正是催生‘以暴制暴’思想的土壤。”
“然而”
方诚话锋一转,逻辑清淅地深入分析:
“承认现实困境,不等于要认同这种极端的解决方式。”
“‘以暴制暴’看似快意恩仇,实则是在用一种更大的恶,去对抗另一种恶。”
“它会引发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撕裂社会契约,最终将整个社会拖入人人自危的丛林状态,这对于弱者而言,将是更大的灾难。”
三位考官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这时,右侧那位一直沉默的女考官忽然追问道:
“但是方同学,你有没有想过,对于那些已经被逼入绝境,走投无路的人来说,这些大道理是苍白的。”
“当他们面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若不奋起反击,可能就将死无葬身之地。”
“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你又该如何劝说他们放弃暴力?”
方诚微微颔首,似乎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
“老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纠错的责任,粗暴地转嫁给身处困境的个体。”
“社会悲剧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失灵,与其去讨论‘能否暴力反抗’这种近乎无解的道德困境,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去根除催生这种困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