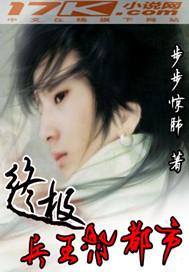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 > 第122章 爱国强国路宣公第一年(第3页)
第122章 爱国强国路宣公第一年(第3页)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康乾盛世”的鼎盛中,将“大一统”推向新高度。康熙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以军事行动巩固疆域,其“满汉一家”的政策推动民族融合;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虽有文化钳制之嫌,却也以“整理典籍”的方式守护文明薪火。此时的“强国”既体现为疆域辽阔、人口增长,也表现为对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从蒙古草原到西南边疆,从雪域高原到东南海岛,“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清晰。
但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击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爱国与强国思想被迫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虎门销烟的壮举践行禁烟强国之志,其组织编译《四洲志》,开“睁眼看世界”之先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器物以图自强,将“强国”的视野从“传统内循环”拓展到“国际竞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洪仁玕《资政新篇》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虽未实践,却已触及“制度革新”的强国命题;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军工、兴办学堂、筹建海军,试图以“器物革新”挽救危局,其“自强”“求富”的口号,承载着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求变的爱国实践。
明清之际的爱国与强国,始终在“守”与“变”中挣扎:既坚守“华夏文明”的根脉,又不得不承认“技不如人”的现实;既眷恋“大一统”的荣光,又必须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这种在苦难中觉醒、在反思中前行的精神,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救亡图存”与“革新自强”的双重使命,推动着中华民族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艰难转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爱国与强国领域,便已形成与东方文明既相似又迥异的精神脉络,其核心围绕“城邦共和国认同”与“公民责任”展开,将个体价值与集体荣耀紧密交织。
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中,“爱国”即“爱城邦”,每个公民都将城邦的独立与荣耀视为生命的一部分。雅典的民主制度虽局限于公民群体,却让“参与城邦事务”成为爱国的直接体现——梭伦改革以“财产等级制”打破贵族垄断,让更多公民参与政治,其“我制定法律,无分贵贱,一视同仁”的理念,将“强国”与“公平”绑定;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宣称“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将雅典的民主、艺术、军事成就视为公民共同的骄傲,而苏格拉底宁愿饮鸩赴死也不愿违背城邦法律,以生命诠释了“公民对城邦的绝对忠诚”。斯巴达则以另一种方式践行爱国:男孩自幼接受军事训练,“为城邦战死”是最高荣誉,其“全民皆兵”的体制让这个城邦以军事强盛闻名,“战死沙场”与“胜利归来”成为爱国的唯一注脚,个体的存在完全服务于城邦的强大。
古罗马从城邦发展为帝国的过程中,爱国与强国思想不断扩容。共和时期,西塞罗提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强调公民对共和国的责任不仅是服兵役,更包括参与立法与司法,其“为共和国而战”的信念,让“爱国”与“维护共和制度”紧密相连。布鲁图斯刺杀凯撒,虽背负“弑君”之名,却自认是为守护“共和传统”这一更大的“国”;加图以“宁死不向独裁者低头”的决绝,彰显了共和派对“自由之国”的坚守。进入帝国时代,“爱国”逐渐演变为对“罗马帝国”的认同,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后,通过修建竞技场、改善民生、扩张疆域,让“罗马和平”成为公民对国家的集体记忆——当士兵在军团旗帜下宣誓“为罗马而战”,当行省居民以“成为罗马公民”为荣,帝国的强大已超越军事征服,成为一种文化与身份的认同。
古希腊罗马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带着“公民共同体”的印记:它不似东方文明强调“忠君”与“大一统”,而更注重个体对城邦共和国的主动参与;“强国”的目标不仅是疆域扩张,更包括制度的优越、文化的繁荣与公民的尊严。这种将“个人自由”与“集体荣耀”相平衡的精神,虽因时代局限存在奴隶制、性别歧视等缺陷,却为后世欧洲的爱国主义埋下了“公民责任”与“制度认同”的基因,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重新焕发生机,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思想资源。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爱国与强国思想被宗教信仰与封建契约层层包裹,呈现出“神权、王权、领主权”交织的复杂形态。此时的“国家”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概念,更多是围绕“领主-封臣”的依附关系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认同,“爱国”往往等同于“效忠领主”“守护领地”,而“强国”则体现为领主庄园的富庶、城堡的坚固与骑士的勇武。
在西欧的封建体系中,封臣对领主的“效忠礼”是爱国精神的直接表达——骑士跪在领主面前宣誓“以我的勇气与武器,为您守护领地、对抗敌人”,这种基于契约的忠诚,让“国”的概念具象化为领主的城堡与庄园。当维京人、阿拉伯人入侵时,领主组织骑士与农奴共同守卫城堡,此时的“守土”既是履行封建义务,也是保护家园的本能,而“强国”的标志便是领地能抵御外敌、保障生产,正如查理曼帝国时期,通过修建要塞、颁布《庄园敕令》规范生产,让领地在动荡中保持稳定,便是最朴素的“强国”实践。
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为爱国与强国披上了神圣外衣。教会宣称“王权神授”,领主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上帝,因此“效忠领主”与“敬畏上帝”融为一体,十字军东征被赋予“解放圣地、扞卫信仰”的神圣使命,骑士们“为上帝而战”的口号,让军事行动超越了世俗利益,升华为对“基督教世界”这一更大“共同体”的忠诚。此时的教堂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领地的精神核心——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既召唤信徒祈祷,也在外敌来临时警示民众,宗教建筑的宏伟与否,成为衡量领地“精神强盛”的标志,而修道院抄写典籍、传播知识,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同时,也以“神的意志”强化着领地内的凝聚力。
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兴起与王权强化,爱国与强国思想开始突破封建壁垒。英国《大宪章》的签署,虽限制王权,却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王国”与“贵族、市民”的权利边界,让“爱国”开始与“维护共同法律”相关联;法国腓力四世与教皇的斗争,强调“王权独立于神权”,推动“法兰西王国”的概念从分散领地向统一国家转变。城市市民则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强国”——通过行会组织规范生产、修建城墙抵御领主盘剥,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威尼斯的航海贸易,让城市成为“经济强国”的代表,市民们以“我是佛罗伦萨人”“我是威尼斯人”的身份认同,孕育着早期的“城市爱国主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一时期的文学与传说,也留下了爱国精神的印记。《罗兰之歌》中,骑士罗兰为守护查理曼大帝的军队撤退,宁愿吹破号角战死也不后退,其忠诚既指向领主,也暗含对“法兰克王国”的热爱;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传说,以“寻找圣杯”“守护不列颠”为核心,将骑士精神与“守护家园”的责任结合,成为中世纪爱国情怀的浪漫投射。即便是农民起义,如英国瓦特·泰勒起义,其诉求虽聚焦于减轻赋税,却也喊出“为王国的自由而战”的口号,让“爱国”不再是贵族专利,开始向下层民众渗透。
中世纪的爱国与强国思想,虽被封建割据与神权束缚,却在“领地守护”“契约忠诚”“信仰共同体”的交织中,缓慢积累着“国家认同”的碎片——当骑士从“效忠单个领主”转向“效忠国王”,当市民从“认同城市”转向“认同王国”,当宗教外衣下逐渐生长出“世俗国家”的意识,近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与强国思想,便在这片土壤中悄然萌芽。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爱国强国领域的认识,也呈现出与欧亚大陆核心文明既呼应又独特的风貌,在各自的地理与文化语境中,将“守护家园”“凝聚族群”“传承文明”作为爱国强国的核心命题。
古印度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与种姓制度、宗教信仰深度交织。在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共同体”的概念通过《梨俱吠陀》的赞歌得以强化,“保卫部落牛群与领地”是武士阶层(刹帝利)的天职,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为正义而战”的俱卢之战,将“爱国”升华为对“达摩(法)”与“王国荣誉”的坚守。孔雀王朝阿育王的“达摩政策”堪称古代印度强国思想的典范——他在征服羯陵伽后幡然醒悟,以“仁政”替代武力扩张,通过修建道路、医院、灌溉工程惠及民生,其敕令中“所有众生皆为吾子”的理念,让“强国”不仅是疆域辽阔,更成为“以善治凝聚多元族群”的实践。而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虽未直接挑战种姓制度,却以“慈悲护生”的理念,为爱国注入了“关爱家园众生”的温情维度。
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文明的崛起中,将“爱国”与“护教”融为一体。穆罕默德提出“凡穆斯林皆兄弟”,打破部落隔阂,使阿拉伯半岛从分散的部落联盟凝聚为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为真主与家园而战”成为穆斯林的神圣使命。倭马亚与阿拔斯王朝时期,“强国”体现为“伊斯兰帝国”的扩张与文明繁荣——巴格达成为“智慧宫”所在地,翻译古希腊典籍、发展代数与医学,将军事征服与文化创造结合;而“迪万制度”(税收与行政体系)的完善,让不同信仰、不同族群的民众在统一治理下安居乐业,此时的“爱国”既是对“哈里发国家”的忠诚,也是对“伊斯兰文明圈”这一精神家园的认同。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时,其“宽容对待基督徒与犹太人”的举措,更让“强国”展现出文明包容的气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爱国精神的象征。
美洲文明在孤立发展中孕育出独特的家国情怀。玛雅人的城市国家以金字塔神庙为中心,统治者通过祭祀与战争维系族群认同,其壁画中“国王率军出征”的场景,将“爱国”表现为对城邦神权与王权的双重效忠;而大规模水利梯田的修建,既是“强国”的物质基础,也体现了“与土地共生”的家园意识。阿兹特克人以“太阳历”为纽带,将农业生产、军事训练与宗教仪式结合,其“向太阳献祭战俘”的习俗虽血腥,却暗含“以牺牲换取家园繁荣”的原始爱国观;特诺奇蒂特兰城的宏伟水渠与市场,见证了这个帝国“以贸易与武力并重”的强国之道。印加帝国则通过“mita制度”(全民劳役)调动人力修建万里驿道与梯田,其“四合一王国”的理念将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纳入统一治理,“效忠印加王”与“守护太阳神赐予的土地”成为爱国的核心,而马丘比丘的巨石建筑,正是这种集体协作与家国认同的物质见证。
非洲大陆的爱国强国思想则扎根于部落共同体与王国文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即太阳之子”的理念将“爱国”与“忠君”“敬神”合一,拉美西斯二世抗击赫梯帝国的卡迭石战役,被刻在神庙墙壁上歌颂“为埃及而战”的荣光,而尼罗河泛滥期的灌溉规划、金字塔的建造,体现了“以集体力量驯服自然”的强国智慧。马里帝国的曼萨·穆萨朝圣之旅,以黄金与慷慨震惊伊斯兰世界,其“修建廷巴克图大学、发展跨撒哈拉贸易”的举措,让“强国”不仅是军事强盛,更是文化与经济的辐射力;而普通牧民对“部落长老”的服从与对“草原家园”的眷恋,构成了非洲内陆最朴素的爱国情感。
这些文明虽未形成现代国家概念,却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为何爱家园”“如何让家园强大”——或依托宗教,或联结土地,或通过制度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为“爱国强国”这一人类共同命题,写下了多元而生动的注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爱国与强国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
日本在天皇与幕府的权力更迭中,将“家国”认同与“武士道”精神深度融合。古代大和政权以“神道教”为纽带,宣称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古事记》中“神武东征”的传说,为“统一国家”赋予神圣起源,此时的“爱国”便是对天皇的绝对效忠。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虽以情爱为主题,却暗含对“大和魂”的细腻书写;镰仓幕府时期,武士阶层崛起,“忠义、廉耻、勇武”的武士道成为爱国的核心准则,楠木正成“七生报国”的誓言,以战死沙场诠释对天皇与家国的赤诚。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通过“参勤交代”制度强化中央集权,而朱子学的传播则让“修身齐家治国”理念与本土“忠君”思想结合,武士们既需“勤练武艺以护藩”,也需“研习学问以强国”,这种“文武兼修”的传统,让爱国与强国在制度与精神层面形成闭环。
朝鲜半岛的爱国与强国思想,始终与“抗御外侮”和“文化传承”紧密相连。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引入中国科举制度与儒家经典,以“儒教立国”凝聚族群,崔致远“虽身在异域,心向故国”的诗文,道尽侨民对家园的眷恋。高丽王朝面对蒙古入侵时,郑梦周“宁为高丽鬼,不作蒙元臣”的殉国,成为“守节爱国”的典范;而《高丽史》的编纂,以文字为故国留存记忆,本身便是爱国的实践。朝鲜王朝时期,李栗谷“经世致用”的思想,将儒学与本土“实学”结合,主张“农桑为立国之本”,其“强国”理念既包含抵御倭寇的军事准备,也注重改良农具、发展纺织的民生建设,而壬辰倭乱中,李舜臣创制“龟船”大败日军,其“以弱胜强”的战绩,让“爱国”成为全民抗敌的精神旗帜。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则在“东西方文明夹缝”中塑造家国意识。基辅罗斯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东正教,以“圣索菲亚大教堂”为象征,将“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结合,此时的“爱国”便是守护“东正教家园”。蒙古西征的压迫下,莫斯科公国以“反抗鞑靼统治”凝聚力量,伊凡一世“收集全俄贡赋”、扩建克里姆林宫,实则以隐忍积蓄强国之力;伊凡四世称“沙皇”,以铁腕统一俄罗斯,其“消灭割据、建立中央集权”的举措,让“强国”与“统一”成为同义词。彼得大帝推行改革,剪胡须、建海军、办工厂,以“向西方学习”推动国家现代化,其“打开一扇通往欧洲的窗户”的决心,让“爱国”从“固守传统”转向“革新图强”;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1812年卫国战争”,将拿破仑入侵时的全民抵抗,升华为“为俄罗斯母亲而战”的民族精神。
东欧各国则在民族独立与外来压迫的博弈中淬炼爱国情怀。波兰哥白尼以“日心说”挑战神学,既是科学突破,也暗含对“民族智慧”的自信;匈牙利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将“爱国”与“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连。这些国家的爱国与强国思想,既带着东正教的精神烙印,也吸收了西欧的启蒙理念,在“守护民族语言”“传承本土文化”“反抗外来侵略”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
东亚与东欧的古代爱国强国思想,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在与外部文明的碰撞中坚守自身根脉,在制度革新与精神传承的平衡中追求强大。这种“守正出新”的特质,让这些地区的家国情怀既带着历史的厚重,也蕴含着应对变局的韧性。
至于东南亚地区,在热带雨林与海洋贸易的滋养中,爱国与强国思想呈现出“本土信仰、王朝认同与海洋文明”交织的独特样貌。这里的“国家”多以河流流域或岛屿集群为依托,“爱国”常与对“神王”的崇拜、对“圣山圣河”的敬畏相连,而“强国”则体现为对贸易通道的掌控、对灌溉系统的维护,以及在多元族群中维系平衡的智慧。
柬埔寨吴哥王朝时期,“爱国”与对“神王”(国王化身毗湿奴或湿婆)的信仰融为一体。吴哥窟的浮雕既描绘神话传说,也记录国王率军征战的场景,将“守护王国”与“侍奉神明”合二为一;而洞里萨湖的“灌溉奇迹”——通过水利工程调节湖水灌溉稻田,让王朝“仓廪丰实”,既是“强国”的物质基础,也被视为“神王庇佑”的证明,民众对家园的热爱,便在对神庙的虔诚与对沃土的依赖中自然生长。
泰国素可泰与阿瑜陀耶王朝,在佛教信仰中构建家国认同。兰甘亨大帝创制泰文、编纂法典,以“法治”与“佛教慈悲”治国,其石碑铭文写道“素可泰无苛政,民皆安乐”,将“强国”定义为“民众幸福”;而寺庙作为社区中心,既是宗教场所,也是抵御外敌时的堡垒,僧侣与民众共同守护寺庙的举动,让“爱国”成为超越阶层的集体行动。阿瑜陀耶作为“东方威尼斯”,通过海洋贸易积累财富,其国王“与中国通好、与伊斯兰商人结盟”的外交智慧,让“强国”不仅是军事强盛,更体现为在多元文明中找到自身位置的从容。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