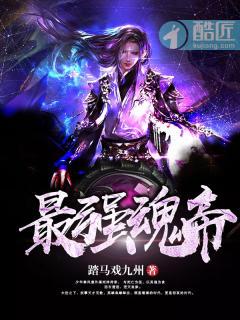趣书网>毕业后打工日记 > 第427章 四二七(第1页)
第427章 四二七(第1页)
清晨五点半,我就醒了。窗外天还没亮,风从小窗缝里吹进来,带着一丝凉意。
今天要做调研汇报,说不紧张是假的。我翻来覆去躺了十几分钟,干脆起身洗漱,冲了个澡,穿了件最像“干事人”的衬衣,打上皮带,皮鞋擦得锃亮,仿佛今天不是要开会,而是要去谈判。
七点出头,我到公司,李姐已经到了,她坐在工位前喝豆浆,一边翻手机。
“来得挺早嘛。”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有备而来?”
我笑:“昨晚练了三遍讲稿,梦里都在讲仓库调度。”
“那你今天不出彩都说不过去了。”她把一叠资料递给我,“这是会议名单和大致议程,张总也会来,你说重点的时候注意节奏。”
我点点头,看着名单上十几个人的名字,有几位我连面都没见过,只听说都是调度、设备、物流、采购那边的骨干和老员工。
九点整,我们会议室准时开会。灯光白得晃眼,气氛一开始就有些紧张。张总坐在正中,李姐在他左侧,我被安排在正对着投影的位置。
开场几分钟,我手心就微微出汗。轮到我发言时,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按ppt一页页讲。
前面几页是流程现状、仓库出入库环节的问题汇总。我特意加了实拍照片、录音纪要,讲得不急不慢,也没刻意夸张。
讲到“货物堆叠无序造成查找效率低下”、“部分调度流程口头传达,无文字记录造成误差”的时候,台下一位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忽然打断我:“你是刚来这的吧?我干这十年了,从来都是这么干,有问题吗?”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认出来了,是调度部的老胡,人称“胡一嗓”。
我没跟他争执,而是点开一段视频监控:凌晨出库时两个夜班员工找货找错,一直到后来打电话问仓库主任才搞清楚情况。
我说:“我没有质疑谁的经验,我只是指出流程存在因‘口头交接’而产生的漏洞。”
老胡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但我感觉空气变得更凝重了。
接着我讲了几个优化建议,比如将纸质交接单变成电子系统扫码、标识清晰化、人员培训统一、设立责任节点……每说一条,李姐都微微点头,但有几个人明显面露不悦。
讲完最后一页时,我收住话,鞠了一躬:“以上是我作为外部调研的初步总结,如有偏颇之处,请各位指正。”
张总点了点头:“讲得不错,确实比较系统。”
还没等他说完,老胡又说话了:“系统确实系统,但年轻人说起来容易,实际干起来不现实。你动电子系统,你问问我们这些干惯了的能不能接受?上了新流程出错了谁负责?”
张总皱眉看了他一眼:“老胡,你的意见我们听,但改革不是为了麻烦你,是为了解决问题。你也别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气氛尴尬了一秒,李姐缓和道:“我们可以试点,选一个仓位先跑一次流程,有问题再逐步修改。不是一刀切。”
我望着她,心里暗松一口气。她这番话,不仅救了场,也给我打了个强心针。
接下来的讨论还是不太顺利,很多人觉得麻烦,或者觉得“你不是我们的人”,说什么都多余。我尽力不与人正面交锋,只把问题说清楚,方案摆明白。
会议结束已是中午十一点半。大家陆续散去,老胡临走时还哼哼:“小孩儿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实际干才知道难。”
我没回嘴,只默默收拾资料。
李姐拍了拍我:“讲得很好,不用理他们,那些人嘴硬,等真换流程换得顺,骂你的人最先拍你马屁。”
我苦笑:“我也不指望他们拍我马屁,但别整天扯后腿就好。”
她抿了口水:“你能坚持下去,五年之后,估计就变成别人怕的老狐狸了。”
我笑:“那时候你还在不在公司?”
她一挑眉:“等你当上副总,我就去你手底下混口饭吃。”
下午,我把会议内容整理成纪要,写了两版,一份对内,一份对张总。晚上回到住处,又收到李倩发来的语音:“我们部门今天也炸锅了,新来的主管把展厅全改了,老员工都在骂她。”
我说:“改革从来都不受欢迎。”
她轻笑:“你这么说,是不是今天你也挨了?”
我叹了口气:“那得看‘挨’的定义,言语攻击算不算?”
“那就你请我吃饭,缓解一下你的精神创伤。”
“等你来郑州吧。”
“那得等到过年了。”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我们那主管还是蛮有一套的,虽然被骂得惨,但她就是不退。”
听着她讲自己的“战况”,我忽然觉得,两地奋斗的我们,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在看似死水的系统里,去捅出点涟漪。
不为别人,只为不浪费自己还在滚烫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