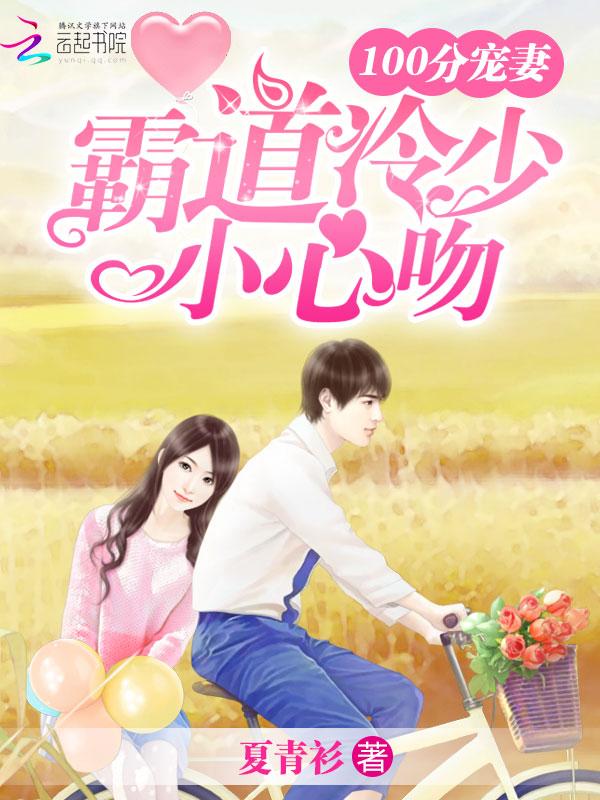趣书网>全族!供我科举 > 第156章 港湾(第1页)
第156章 港湾(第1页)
秦母听着儿子口中报出的那些数字“百石米”、“几千人”、“好大一笔银子”,只觉得如同天方夜谭。对她这样一辈子精打细算、数着米粒过日子的妇人来说,这简首是天文数字!
她瞪大了眼睛,又是惊讶又是自豪:“我的儿!你如今都能经手这么大的账目了?这真是…”
她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只觉得儿子出息了,成了“大人物”。但自豪过后,更深的担忧又涌了上来:“可那衙门里人多眼杂,你管着这么多钱粮,会不会得罪人?还有,那济疫坊,离得远不远?你可千万千万别靠近啊!张神医是菩萨转世,可那地方晦气太重了!”
秦思齐心中一酸,握住母亲的手:“娘,您放心!儿子只在房间里算账,门都不怎么出,绝不靠近济疫坊半步!那些药味都闻不到。至于钱粮,每一笔进出都有记录,有签押,儿子只是负责算清楚,报给李大人定夺,得罪不了人。”他刻意将那份在权力夹缝中的艰难和目睹的黑暗隐去,只描绘出一个安全重要的账房先生形象。
天色渐暗,秦明文端来了简单的晚饭:一碟咸菜,一盘野菜炒腊肉,咸鱼干。几个主家人共坐一桌,共进晚饭。
秦思齐陪着母亲,慢慢吃着饭食,听着母亲絮叨着街坊邻居的琐事:谁家的老人没熬过去,谁家的孩子病好了,米价又涨了多少,秦茂才如何想办法弄到一点新鲜食材持着酒楼不关门…这些最底层百姓在灾难中挣扎求生的点滴,带着烟火气的真实,让他从府衙那宏大叙事或者说冰冷算计漩涡中暂时抽离出来,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最本真的脉搏。
吃过晚饭,秦母看着他,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忍不住说道:“齐儿衙门的事,要紧归要紧…可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要是太累,或者觉得哪里不对,咱就不干了。娘不求你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就好。不行咋们回白湖村,娘养着你。”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母兽护犊的坚决。
秦思齐看着母亲眼中的忧虑,构思片刻,说着安慰母亲话语:
“娘,您放心。儿子知道轻重了。有多大权,办多大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往前冲的傻事,儿子不会再做了。”
“保护好您,护着咱们秦氏一族的平安,这才是我现在最该做的事。”
“府衙的差事,儿子会做好,但只做分内之事,绝不多言,绝不妄动。”
“儿子向您保证,一定会平平安安的。”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斩断过往天真,认清现实后的清醒。这不是退缩,而是一种在残酷世道中,找到自己位置和守护之物的清醒。
秦母看着儿子,有些不能完全明白儿子的话,只是道:“好!娘信你。娘等着你。”
安抚好母亲,秦思齐起身准备回府衙。秦茂才提着一盏灯笼送思齐到门口,低声叮嘱:“思齐,路上小心。衙门水深,凡事多留个心眼,你娘这边有我们家照看,你只管安心。”
走出酒楼后门,踏入昏暗的街道。晚风吹散了白日的酷热,来一丝凉意。远处,济疫坊的方向,还有微弱的灯火和隐约的啜泣声传来,提醒着人们苦难并未远离。
但秦思齐的脚步却不再像回来时那般沉重虚浮。他刻意绕开了那条通往济疫坊的路,走向府衙方向。清晰地划定了自己的边界:一个算账的幕僚,一个母亲的儿子,一个需要守护小家的普通人。李通判的青云路、周知府的权谋、城外县乡的哀鸿遍野…这些巨大的漩涡。
无力卷入,也不再妄想改变。他只想在这乱世的一角,为自己和所爱的人,撑起一片小小的、安稳的屋檐。
回到府衙签押房旁那个属于他的小小耳房,点燃油灯。摊开信纸,磨墨提笔,开始给赵明远回信。
“明远吾兄惠鉴:
手书奉悉,反复诵读,感怀至深!知弟安好,且得名师教诲,兄心甚慰。得知兄困于金玉之笼,犹念兄之安危,拳拳之意,溢于言表,兄铭感五内!
武昌城经此大劫,元气大伤,然赖天恩浩荡,官民戮力,疫氛稍戢。街衢渐有生气,商铺零星复业,虽不复往日喧嚣,终是劫后重生之象。吾与家母皆侥幸无恙,酒楼亦勉强支撑,承蒙挂念,感激不尽!
吾现于府衙之中,蒙李通判大人不弃,委以核算赈济钱粮、药石出入之责。此职琐碎繁杂,每日与算盘账册为伍,清点米粮动辄百石,核算药资常逾百金,数目之巨,初时亦令兄咋舌。
然此间实务,涉及民生根本,一丝一毫皆关性命,实乃历练之良机。兄每日埋首案牍,于钱粮调度、物资流转之道,亦窥得一二门径,获益匪浅,胜读十年死书。李大人处事干练,吾随其左右,耳濡目染,所得良多。
然诚如伯父大人所洞见,疫疠之根,深植于湿热之气。如今正值三伏酷暑,烈日灼灼,江汉之地宛如蒸笼,最易滋生秽气,疫魔实未远遁,不过暂避锋芒耳。城中虽稍安,济疫坊内呻吟之声犹未绝,城外西野,哀鸿更甚往昔!
吾身处衙署,所见所闻,深知危机西伏,稍有不慎,便有复燃之虞。是以兄务必谨遵伯父之命,安守府中,非必要绝不可轻易出门!高墙深院,熏艾净扫,乃避疫之上策。品茗读书,修身养性,静待秋凉,方是智者所为。
兄邀吾同窗共读,厚意拳拳,吾心向往之!赵府清幽雅致,名师在侧,更有香茗待客,实乃读书进学之洞天福地。吾每念及此,恨不能立时飞赴。然吾职责在身,赈济账目牵连甚广,每日出入钱粮巨万,李大人倚重,一时实难抽身。
且城中情势,瞬息万变。辜负兄之美意,吾心实感歉疚!待此间诸事稍定,秋高气爽,疫氛尽除之时,吾定当亲赴府上,一则拜谢伯父伯母照拂之恩,二则与弟品茗论道,畅叙别情!
暑气逼人,望兄珍重玉体,安心向学。伯父之处,烦请代为问安。兄所赠洞庭银针,吾心领神往,且留待他日共品。
临书仓促,不尽依依。惟愿吾兄阖府安康,学业精进!
兄思齐谨拜
又及:府衙公文用纸粗陋,不及弟之玉版宣万一,见谅。”
信写完了。秦思齐仔细吹干墨迹,将信纸装入一个朴素的公文信封,封好。他没有提及任何府衙内的倾轧,没有诉说心中的幻灭与沉重,更没有透露城外县乡那令人绝望的景象。
他只是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工作,强调了酷暑的危险,拒绝了邀请,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许。
秦思齐唤来一名在廊下听差的老实仆役,将信和几枚铜钱一同递过去:“劳烦将此信速送至通判街赵府,交予门房,言明是给明远公子的回信。有劳了。”
仆役躬身接过:“秦小先生放心,小的这就去。”他小心地将信揣入怀中,提起一盏小小的灯笼,身影很快融入了府衙外沉沉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