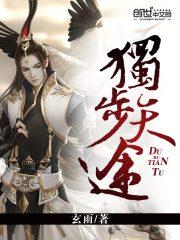趣书网>大唐:全能太子,李二直呼内行 > 第57章 火种烧到了宫墙外(第2页)
第57章 火种烧到了宫墙外(第2页)
武媚娘伸出手指,轻轻抚过“西市十三灯”的标记,眼神复杂。
“若我现在说,这灯是我点的,还有人信吗?”她突然问道,声音低沉而沙哑。
法融笑着摇了摇头,说道:“信不信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肯为别人点灯。”
武媚娘沉默了。
是啊,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盏灯已经不再需要她来点燃,它自己便能出光芒。
几日后,徐惠召集柳如意和韩文博,共同商议《民医灯规制》。
徐惠建议,应该统一民医灯的灯型、编号、值守轮班,并且设立“灯使碑”更新机制,将每个灯的由来和值守人的信息都记录在石碑上,方便百姓查阅。
然而,柳如意却摇了摇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一规就死,”她说道,“我们当初为何能立信?因为灯是活的,人走到哪,灯就亮到哪。如果制定了统一的规制,反而会束缚住百姓的热情。”
徐惠听后,陷入了沉思。
柳如意的话很有道理,如果强行制定规制,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沉吟良久,徐惠终于做出了决定。
她改令为“灯制备案”,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设立灯的样式,只需要将灯的形制和值守人报备给东宫,东宫只负责存档,不进行任何干预。
消息传出,百姓们纷纷称赞:“官不压灯,灯自生光!”
是的,官府不干预,百姓的创造力是无穷的。
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点亮属于自己的灯,照亮自己的家园。
当夜,李承乾负手立于东宫那间积满灰尘的旧灯政房,看着案几上堆积如山的灯式图样,不由得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意。
竹灯的朴拙,陶灯的厚重,铁皮灯的实用,甚至还有那盏用鱼骨小心镂空,罩着鲛绡的海灯,无不展现着大唐百姓的巧思与热情。
他随手抽出一张略显稚嫩的画作——灯下,一对母女紧紧牵着手,旁边歪歪扭扭地题着一行字:“我娘病好了,我也能点灯啦!”那份纯真与喜悦,仿佛透过纸张,直接撞进他的心房。
“殿下。”
忽闻飞骑统领薛仁贵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打破了这份静谧。
“城南药园昨夜失火,烧了半亩苗地。”
李承乾面色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查过了?”
薛仁贵抱拳道:“查了,是园工煮药时不慎,忘熄炉火。”
“嗯。”李承乾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目光却透过窗棂,望向长安城南的方向。
那里,慈恩庵的灯火早已熄灭,只剩一片黑暗。
他收回目光,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低声喃喃自语,像是在说给薛仁贵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她没烧,可她想烧的时候……这星星之火,已经不怕这高高的宫墙了。”
灯,已在野。风,已成势。
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李承乾缓缓踱步至窗前,伸手拂去窗棂上的尘土,任由清冷的月光洒在他俊朗的面庞上,眼神深邃而悠远。
“灯制备案”推行一月,长安坊间灯火更盛,然……他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眼神瞬间变得锐利。
“殿下,怎么了?”薛仁贵察觉到太子的异样,连忙问道。
李承乾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投向远方,那里,似乎有什么正在悄然生。
“去把高履行叫来。”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
薛仁贵领命而去,留下李承乾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注视着长安城中那一片璀璨的灯火,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