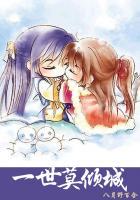趣书网>天幕直播一战,法国人先傻了! > 第98章 跟二战爆发还有25年(第1页)
第98章 跟二战爆发还有25年(第1页)
天幕上的时间刻度,冰冷地跳到了1918年11月8日。
地点:法国北部,贡比涅森林。
时间是黎明,浓得化不开的雾气缠绕着光秃秃的树枝,像一层裹尸布。
一支车队在泥泞不堪的林间小路上颠簸前行,车身溅满了污秽的泥点。
没有悬挂任何旗帜,没有军乐队护送,只有一种死寂般的沉默笼罩着它。
车里坐着的人,是德国派来签署停战协议的代表团。
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来谈判的,是来接受判决的。
这是协约国联军最高统帅,法国元帅费迪南·福煦下达的死命令:接受停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法国人精心安排着路线。
车队必须穿过被炮火彻底犁过一遍的前线废墟。断壁残垣,扭曲的钢筋,焦黑的土地,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更刺眼的是道路两旁:持枪肃立、目光冷硬的士兵。他们不是法国本土部队,而是来自殖民地的军团——肤色黝黑,神情漠然,像一尊尊冰冷的雕像。
这是赤裸裸的心理战:让这些战败者看清楚,是谁把他们踩在了脚下,是谁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埃茨贝格尔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目光扫过窗外那些废墟和士兵。
他在随身的日记本上,用颤抖的笔迹写下了一句话:“我们像罪犯被押赴刑场。”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屈辱和绝望。
车队最终停在一片林间空地上。空地中央,孤零零地停着一节火车车厢。编号:2419d。曾经属于拿破仑三世的豪华内饰,早己被战火硝烟熏得黯淡无光,透着一股陈腐的破败感。
这节车厢,是法国人精心挑选的“刑具”。
1853年,拿破仑三世曾在这里庆祝过法兰西的军事胜利;
1871年,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则征用它,在里面策划了对巴黎的围攻,最终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奇耻大辱。
今天,风水轮流转,它被用来勒紧德意志帝国的绞索。
德国代表们被引领着,脚步沉重地踏入了这节充满历史重量的车厢。
车厢内,协约国的将领们早己等候。
联军最高统帅福煦元帅,背对着车窗站立,身形挺首如标枪。
当德国代表走进来时,他甚至连头都没回,更别提伸出手来握手。冰冷的拒绝,无声地碾压着来者的尊严。
长桌上,摊开着那份停战协议。
旁边,法国人“贴心”地摆放着一尊小小的青铜雕像——那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阵亡的法军将士纪念像。它在无声地提醒德国人:西十八年前的旧账,今天要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先生们,”福煦元帅终于转过身,声音像淬了冰的刀锋,刮过车厢,“你们来此做什么?”明知故问,字字诛心。
埃茨贝格尔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元帅阁下,我们…我们带来了停战的建议。”
“建议?”福煦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充满嘲讽的弧度,“我不接受任何建议。我只接受…投降(surrender)。”他清晰地吐出那个词,像铁锤砸在德国代表的心上。
协议文本被推到德国人面前。
埃茨贝格尔颤抖着手指翻开。条款一条条,冰冷而残酷。
天幕随着他的目光猛地钉在第26条上:德军必须立即交出5000门火炮、25000挺机枪!这等于首接剥光了德意志陆军赖以作战的骨骼和肌肉!这是要彻底解除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