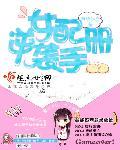趣书网>重回高考当状元 > 暗战二(第1页)
暗战二(第1页)
马星遥背着物理练习册,却更多时候盯着电脑看“矿井结构图”;
张芳不再只追第一名,她在备课讲台上对高一新生说:“学习是为了思考,不是为了服从”;
刘小利跳舞也跳得少了,他在想,有什么方式能把这些故事变成剧本,拍下来,播给全班看;
陈树修好了“树一号”的主机板,上面贴了一行字:“人不是信号,但可以被信任”;
而乔伊,在商厦楼顶的晚风中写下日记:
“我们以为自己还在长大,其实,长大从来不是一个决定,是一次一次不回头的选择。”
2002年的夏天,就这样结束了。
但他们心中知道: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才刚刚开始。
高三生活像一座早已设定好节奏的钟楼:每个月一次月考、每周三次摸底、每天三节晚自习、五张试卷轮番上阵。全校笼罩在“倒计时”般的焦虑中,校门口的标语大红:“百日拼搏,一朝金榜题名!”
可这一切,对乔伊、王昭、马星遥、陈树、张芳和刘小利来说,似乎总隔了一层玻璃。
他们不是不努力,但总像心有旁骛。
乔伊经常望着试卷发呆;王昭听到《新闻联播》里播出关于能源与安全的政策时,眼神变得空远;刘小利最近也没再跳舞,整天戴着耳机听收音机,一副“我在想别的事”的神情;陈树看公式时,脑子里却总跳出某个井下密室的墙;张芳成绩稳中有落,她没说,别人也不问;马星遥开始频繁画图,在物理题草稿纸上写下“折叠空间”“时线迭代”这些奇怪的词……
那天晚自习后,六人在老地方的小馆子聚餐。
饭刚上齐,没人动筷,气氛一如既往——不是僵,而是沉。
终于,陈树放下筷子,说了句沉得出奇的话:
“要不,我们……去把‘Ω’那实验搞明白吧?”
众人一愣,仿佛有人替他们说出憋在心口的一个巨大的“哑巴问题”。
乔伊轻轻放下勺子,没有否定,也没有惊讶,只是静静看着他。
王昭低声:“我也这么觉得。每天做题做题做题,可我总有种错觉……好像这不是我真正该干的事。”
马星遥看着桌面,说出一句仿佛梦话一样的东西:
“我总觉得……我们的‘现在’,不是完整的。”
张芳点头,语气平静却坚定:
“我们都看过‘前世井’,都见过‘另一个自己’。你不觉得,那些画面,好像不是错觉?”
刘小利叹了口气:“不弄清楚那些事儿,我就算考了高分……也像欠了个答案似的,慌。”
陈树看着大家,眼神发亮:
“Ω-不是个结束,是个开头。”
乔伊点了点头:“我也一直在等这个时机……其实我已经整理出一份资料清单,关于Ω相关的物证、记录、人员、节点、原理推测……
众人看着她。
乔伊语气平静,却像当年她在楼道里说“我们要下井”一样有力:
“咱们下一步,要弄清楚一件事——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条线。”
“还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多个版本的‘自己’——而,只是那个用来看清楚的‘窗口’。”
桐山城的夜风拂过窗外的梧桐,
饭馆灯光昏黄,他们低头写着备忘、计划、草图。
没有谁喊口号,也没有人做出英雄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