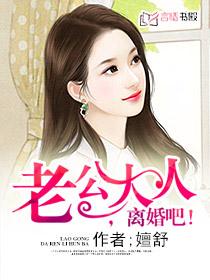趣书网>综视权臣 > 第103章 远赴党项(第1页)
第103章 远赴党项(第1页)
文德殿内,气氛凝重得仿若能拧出水来。
官家眉头紧锁,手中的朱笔停在半空,迟迟未落下,目光死死地盯着面前密阁递上来的折子。
折子上写道洛阳元家叛宋,影司元仲辛有叛宋嫌疑,如同一把尖锐的匕首,首首地刺痛了他的眼。
“元仲辛”官家低声呢喃,声音里满是疑惑与思索,“那小子,不是刚刚调入马渊手下听差,当真会叛宋?”
官家想起马渊前几日上奏的万言书,再加上现如今的元仲辛一事,决定召见马渊。
对着孙内侍吩咐道:“你即刻前往广安伯府,传朕口谕,宣广安伯速速进宫,朕要与他好好商议西北战事,至于元仲辛此事暂且按下,待朕与广安伯商议完正事,最后再看看如何处理此人。”
孙内侍领了旨意,不敢有丝毫耽搁,转身便匆匆离去。
不多时,孙内侍带着两个小内侍,来到了广安伯府。
门房见是宫里来的人,哪敢怠慢,麻溜地跑进去通报。
马渊正在书房思考元氏族人叛宋一事对元仲辛的影响。
听闻宫里来人传召,先是一怔,随即反应过来,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与期待。他迅速整理了一下衣衫,快步来到前厅。
孙内侍见了马渊,上下打量了一番,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尖着嗓子说道:“伯爷,官家有一些西北党项的事情要问你,特命咱家来传你即刻进宫,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别误了时辰。”
马渊心中一喜,忙拱手行礼:“多谢孙内侍告知,马某定当速速随孙内侍进宫,不敢有半分耽搁。”
一行几人快步出了伯府,登上早己等候在府外的马车,朝着皇宫方向驶去。
马渊坐在摇晃的马车里,手紧紧攥着袖中的一份小册子,那是他连夜修改的关于对付李元昊的几条计策,心里头既紧张又期待——他知道,这一去,或许能改变大宋在西北的困局。
文德殿的金砖被宫灯照得发亮,马渊跟着孙内侍跨过门槛时,靴底蹭过地面发出轻响,倒让他紧绷的心弦松了半分。
官家正坐在龙椅上,手中还捏着那份万言书,见他进来,抬手免了跪拜礼,目光里带着几分审视,更多的却是急切:“爱卿,你那万言书里的见地,朕瞧着透彻。只是西北战局瞬息万变,你可有更新的计较?”
马渊深吸一口气,袍角在身侧轻轻一拂,躬身道:“臣不敢称计较,不过是近日反复推演,偶有三策,斗胆呈给官家参详。”
“哦?三策?”官家身子微微前倾,朱笔往御案上一搁,“爱卿速速道来。”
“臣以为,下策在于守。”马渊声音稳了稳,目光扫过殿中悬挂的舆图,西北那片褶皱般的疆域仿佛在眼前铺开。
“可即刻调陕西、河东驻军往边境增防,加固城寨烽燧,任凭党项如何挑衅,只守不攻。李元昊虽勇,麾下铁骑却耗不起持久战,游牧部族粮草仰仗劫掠,我军闭城死守,拖上三五年,其部众自会生乱。”
官家指尖在御案上轻点,眉头微蹙:“只守不攻,岂非要让西夏小儿看轻了我大宋?”
“官家明鉴,”马渊抬头迎上视线,“下策虽显被动,却能保边境无虞,待其锐气耗尽,再做后图。”
“那中策呢?”
“中策,守中带攻。”马渊语气陡然凌厉,“一边依下策固防,一边遣死士潜入党项腹地。李元昊虽统一诸部,但其境内吐蕃、回鹘旧部多有不服,党项部之中亦有觊觎权位者。可联络这些势力,许以重利,令其为我军刺探军情,甚至在战时倒戈。待摸清其主力动向,便以精锐突袭,打掉他几处粮草重镇,或是在野战中击溃其王牌,断其扩张的底气,折其野心。”
官家眼中闪过精光,忽然笑了:“这法子倒有几分合纵连横的路数。只是联络反正,怕是不易。”
“世间事,难在人为。”马渊道,“党项新立,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只要饵给得足,总有肯冒险之人。”
“那上策?”官家追问,声音里己带了期许。
马渊深揖及地,语气郑重:“上策,当借外力。党项地处辽宋之间,如同一把楔子。李元昊野心不止于河西,其己经吞并甘凉、占据河套,羽翼丰满,己成大患。可遣能言善辩之臣出使辽国,若我大宋愿与辽国约定,南北夹击,划定疆界,共同压缩党项的生存空间,辽国未必不肯应允。如此一来,党项腹背受敌,纵有李元昊天纵之资,亦难回天。”
殿内静了片刻,只闻宫漏滴答。官家忽然起身,踱到舆图前,手指重重点在兴庆府的位置:“南北夹击好一个上策!只是辽国向来贪婪,怕是要狮子大开口。”
“取舍之间,在于利弊。”马渊道,“割些岁币,总好过让党项坐大,日后兵连祸结,损耗百倍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