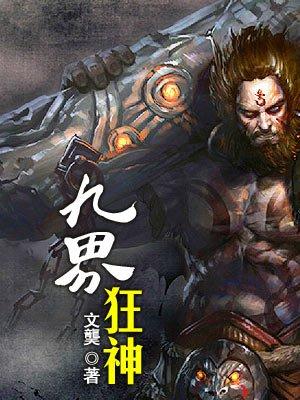趣书网>我,三清合一,玩弄诡异 > 第133章 发展(第3页)
第133章 发展(第3页)
如果不是粮草紧缺,他也不会冒险。
穿过城区,他们来到了一处喧嚣震天的巨大工坊区。
这里没有传统铁匠铺的杂乱无章,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分工明确的“流水线”。
有人专门负责熔炼铁水,有人负责锻打粗胚,有人负责精细打磨,有人负责淬火,最后有人负责组装。
“这也是孙先生的手笔,”赵承运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叹,“他称之为‘标准化生产’。
如今我们打造一支箭,从原木到成品,只需要过去十分之一的时间。
而且所有箭矢的重量、长度、箭头样式都完全一样,极大地提升了弓兵营的齐射精度。”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清瘦的身影,正满头大汗地同一个膀大腰圆的工匠大师傅争论着什么。
他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脸上还沾着几道黑色的炭灰,手里拿着一张画满了奇怪符号和线条的图纸。
“孙先生!”赵承运喊了一声。
那人回过头,正是孙乐安。
他看到李常青,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爆发出巨大的惊喜,连忙小跑过来,恭敬行礼:“李先生!您您怎么来了!”
李常青的目光落在他手中的图纸上,那上面画着的是一个弩机的零件分解图,旁边用简化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标注着尺寸。
孙乐安用现代知识提速发展的痕迹,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在忙什么?”李常青问道。
“回先生,”孙乐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在改良床弩的击发装置。用杠杆和齿轮结构,可以节省八成的上弦力气,还能让弩箭的射击角度更加稳定我大学就是研究的这个方向,还有系统辅佐我,更是如鱼得水。”他一说起自己的专业,便有些滔滔不绝。
李常青静静地听着,最后目光越过喧闹的工坊,望向了更远处。
在那里,有一排排整齐的屋舍,里面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
“那是”
“是孙先生创办的‘启蒙学堂’,”赵承运答道,“他说,想要天下,不能只靠我们这一代人。得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懂得明辨是非的道理。”
听到这里,一首沉默的林啸,终于有了动作。
没有泪水,因为僵尸不会流泪,但那份发自灵魂深处的悲怆与悔恨,却比任何哭声都要来得惊心动魄。
他看到了,他全都看到了。
如果如果他的军队能有这样充足的补给,如果他的同僚不是叛徒,如果朝廷能有赵承运这样的远见和孙乐安这样的奇才
那么,覆灭的,本该是胡人!
李常青,对赵承运和孙乐安做出了最终的评价。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