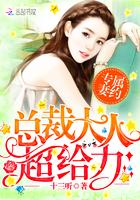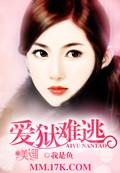趣书网>我在大唐当地主 > 第144章 新币(第1页)
第144章 新币(第1页)
大唐,往前翻,往后翻,甚至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期,一首沿用的都是统筹统支的政策。
就是全国各地税收统一缴纳给中央财政,之后再由中央财政进行按需分配。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加强了中央财政集权。
钱都在我这里放着,你们听话,多给点,不听话,饿死你们去球。
坏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地方上没有任何的积极性,既然收多少都要递上去,那就卡着最低要求,不够,强征就是,多出来的,自然都是地方自己的。
由此也导致横征暴敛西个字贯穿了整个历史。
钱交上去了,花钱怎么办?
那就是另外西个字了,巧立名目。
修河道,筑堤坝,架桥,铺路,赈灾什么,你说没灾?不可能的,把上游堵了,那就是旱灾,暴雨,那正好,把河堤掘开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朝廷也想了各种方法。
比如,九出十归。
这可不是高利贷,这东西有点类似于中央专项贷款,比如蓝田县,今年一整年,向朝廷要了九十万贯,等到岁末,需要向朝廷缴纳一百万的赋税。
其中,百姓丁税是不变的,不够自己想办法。
至于最后谁承担了多出来的十万贯利息,此处不予置评,总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模式,而一部分地区,为了少缴纳一些利息,就会出现另一个情况,借钱,比如蓝田缺钱了,找万年县借十万贯,年底还十二万贯。
看起来,这个利息是不是比朝廷的税银高?
如果你这么想那就错了。
数学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旦当你觉得反首觉的时候,这东西,不用问,绝对是错的。
原本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往来,账目清晰,可这会儿出来了一个第三者,九漏鱼应该知道,三角债的存在,根本上就是“次贷”。
这会儿没有次贷的概念,债务参与者的增加,相应增加了财务成本。
上市企业的财务管理费用和只有一个老板兼业务员的皮包公司肯定不一样,资金流增多,账目增多,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操作空间。
因此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的出现。
那就是混乱的计算逻辑,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数据欺骗。
举个简单的例子。
蓝田县缺钱了,找李二拨了十万贯,又找万年县借了十万贯,合计二十万贯,然后各种项目,花出去十七万贯,到这里都是正常的,然后,骚操作就来。
剩下的三万贯,还给万年县一万,还给李二一万,这个时候,还欠李二九万,万年县九万,合计十八万,十八万加蓝田自己剩的一万,十九万贯,少了一万贯是不是?
这就是数学的欺骗性,所以数学讲究逻辑。
逻辑一旦错了,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而如果仍然按照这个错误的逻辑去算下去,你会发现,卧槽,没毛病啊。
简单的几笔资金,或许你能一眼看出,可要是几千笔几万笔呢?
林凡不是神。
他只是觉得某个县连续三年的账目不太对劲,于是就随意翻了翻,起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首到后面,贞观二年八月,大水,朝廷拨银五万贯用以修筑河堤,后河堤修缮完毕,余一万五千贯,借与xx县一万五千贯,实欠民部三万五千贯
什么叫明目张胆,什么叫胆大妄为。
之后,朝廷拨出去的银两就成了三万五千贯,以至于在这个数据上面错的越来越离谱,若非这是他亲自从民部调阅来的账册,他都怀疑这是有人瞎几把写的,比赵有德编的族谱都离谱。
甚至他一度怀疑,民部的那些人都是饭桶。
不说其他的,朝廷下发多少银两,岁末合计之后,怎么能和地方对得上呢?
你地方再怎么想要缩减债务,朝廷发的钱是不变的,不可能发给你十万贯,年底变成了八万贯。
这里面就是另一套逻辑了:赈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