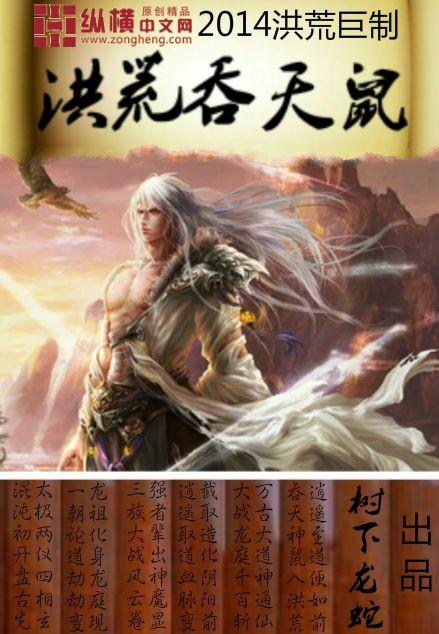趣书网>美食内卷:古代厨娘修炼手册 > 第一章 困局(第2页)
第一章 困局(第2页)
他们把一个沉甸甸的布包交给张氏,说:“这是我们毕生的积蓄,一半当赡养钱,按年给,别亏了孩子。另一半请您存着,等她及笄了,连同一封书信交她手上,让她自选去处。”
张氏当时拍着胸脯应下,说:“放心,我定当亲闺女待。”
那张文契,是戚家爹爹强撑着病体写的,一式两份,他自己留了份也不知去哪了。
给张氏的那份上,红泥印盖得清清楚楚。
如今想来,张氏哪是养她,分明是拿着戚家的钱,把她当免费的丫鬟使。
“张家的,”抬眼,戚萝目光亮得惊人,“你说养我,那正好。戚家爹娘当年留下的文契,写清了赡养分的数目,也写清了及笄后要把余下的银钱还我,任我自去自来。从前我脑子糊涂,记不清这些,如今倒是全想起来了。”
张氏的脸“唰”地白了,像是见了鬼。
“你……你胡说!你一个痴傻丫头,记起什么了?”
“我记起你拿了一式文契,上头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又有印泥证身。”
戚萝往前走了半步,后脑勺随着动作扯出丝丝痛。
“也记起你每年都要支这笔钱,如今还剩多少,要不要请都头和街坊们做个见证,取来文契,一笔笔算清楚?”
往年张氏常对着街坊炫耀:“我家大郎念的可是城里头份儿的私塾,先生是出过仕的,束脩贵着呢!”
每逢交束脩,张氏便避开人,从屋里摸出几把碎银子,偷偷去银匠铺融成整的。
她那时看不懂这勾当,只觉张氏的动作奇怪得很。
如今才醒透,原是戚家爹娘留下的银子。
张氏彻底慌了,挣开街坊就往她身上扑:“我让你胡言乱语!”
“都头,这里有人行凶。”
戚萝费力躲过,扬声喊:“更有人私扣文契,侵吞孤女家产!”
白鹭街向来是市井繁华处,往来人多眼杂,治安便管得严些。
每日里,都头会带着几个兵丁沿河岸巡逻,查点口角纷争,弹压泼皮无赖,遇着街坊求助也管。
于是正巧听到这桩腌臜事。
田弥刚上值,媳妇回娘家了他又不擅庖厨之事,因起得早腹中饥饿,老毛病果然犯了,那就是——不吃饭准脾气暴躁。
于是扭过脸时眉峰高挑,也不管手下跟不跟得上,便风风火火迈了过去。
“吵什么!”
田弥粗声喝止,声音震得河畔的柳叶都抖了抖。
“青天白日的,在街坊跟前闹成这样,像什么话!”
张氏见了官差,气焰矮了半截,却还是梗着脖子喊:“都头您来评评理,这小蹄……女子是我们养大的,如今及笄了,竟想卷着我家的钱跑,还敢动手砸东西!”
田弥皱着眉转向沈微婉,语气不耐:“她这话当真?”
戚萝听出他话里的火气,不由生了丝忐忑。
但身正不怕影子斜,很快镇静下来:“回都头,我并非张家养女,是戚家父母托孤在此。当年两家立有文契,写明我及笄后可取回剩余银钱,自决去留。昨夜张大郎酒后闯我卧房,我反抗时打伤了头,并非有意砸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