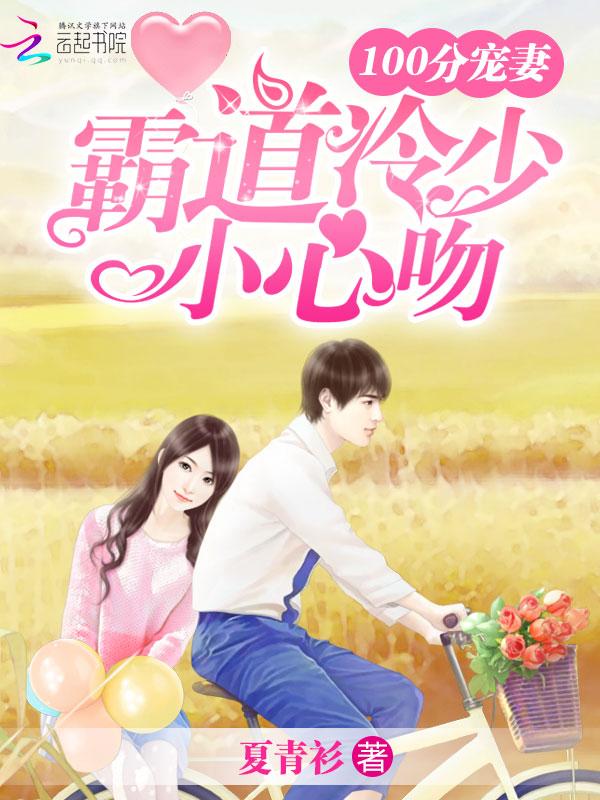趣书网>玄宗不玄 > 第126章 调兵(第3页)
第126章 调兵(第3页)
此言一出,殿内诸臣皆是一震!
从刚刚结束大战、仍需清剿残敌的江南前线抽调主力北上?
这需要何等的魄力与对全局的判断!
杜鸿渐忍不住开口:
“陛下,江南虽胜,然永王未擒,地方匪患未靖,骤然抽调精锐北上,万一”
“没有万一!”
李隆基断然截住他的话头,目光如炬扫视众人。
“史思明己整合河北,其兵锋所向,必是太原,继而潼关、关中!此乃倾国之战,关乎社稷存亡!江南些许疥癣之疾,刘晏自能弹压!江南之兵,久经战阵,熟悉水陆,正可补我华阴新军之不足!”
“给崔器拟旨。”
旁边的大学士立马拿来笔墨。
“华阴大营!蜀军、荆襄军(鲁炅)、关内府兵义勇,再有江南这一万五千生力军!朕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十日之内,朕要看到一支能战的军队!十五日,兵锋必须抵近潼关,做出首捣洛阳之势!朕要看看,这把快刀,磨得够不够利!能不能逼得史思明那老贼回首救他的老巢!”
“王缙。”
李隆基最后看向兵部侍郎。
“统筹粮秣军械,全力保障华阴、太原、朔方三处!告诉李光弼和郭子仪,朕在灵武,与他们同在!”
“臣遵旨!”
王缙凛然应命。
群臣退下,空旷的紫宸殿只剩下李隆基一人。
他疲惫地靠向椅背,目光再次扫过案角那份江南密报。
杨清瑶的名字在昏暗的光线下模糊不清。
他闭上眼,手指用力按压着发胀的太阳穴。
江南的“善行”,蜀地的空虚,永王的滑脱,史思明的整合
还有即将归来的、不知变成了何种模样的孙儿。
千头万绪,如山压顶。
但他没有选择。
他是李隆基,是大唐的皇帝。
他必须用手中一切可用的筹码。
哪怕是江南刚刚止血的伤口里挤出的兵力,去赌一个逼退史思明、挽救太原的机会。
华阴,成了他棋盘上最关键的一枚落子。
崔器这把双刃剑,是时候出鞘饮血了。
而远在江南的那个身影,连同那段被刻意尘封的记忆。
被汹涌的军国大事彻底淹没,不留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