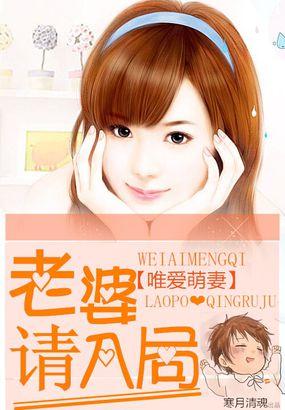趣书网>第三十年明月夜电视剧免费观看 > 第17节(第2页)
第17节(第2页)
&esp;&esp;不,此人虽美如珠玉,又装的孤苦可怜,博人同情,其实内心,比蛇蝎还毒!
&esp;&esp;李楹藏在袖子的手又狠狠捏了下断甲处,她疼的一哆嗦,目光也清明起来,她看着崔珣,语气十分平静:“我既答应了盛云廷,便不会食言。六年前,天威军被困,盛云廷奉郭帅之命,前往长安求援,途经长乐驿之时,被中郎将沈阙和王燃犀诱骗进长乐驿,乱刀砍死。王燃犀怕冤魂缠身,所以一道镇魂符,将盛云廷魂魄镇于尸身,整整六载,不得出。”
&esp;&esp;崔珣手中白麻纸已被抓皱,他脸色苍白如鬼魅,胸膛起伏不定,呼吸也愈发急促,似乎在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痛苦,李楹慢慢道:“如今王燃犀死了,盛云廷
&esp;&esp;的魂魄也终于逃脱桎梏,他魂魄得出后,
&esp;&esp;要再查李楹的案子,必然绕不去太后。
&esp;&esp;就像崔珣所说,要看到底是谁杀了李楹,就看谁是此事的最大受益者,而无人否认,李楹之死,最大受益者,就是太后。
&esp;&esp;崔珣买通内侍省小吏,取来了三十年前太后身边近婢出入宫记录,他秉烛翻阅了好几晚,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白日还要忙碌察事厅事宜,几天下来,人又清瘦了一圈,这几日,太后倒是召见了他一次,本来他以为太后是要因王燃犀之死兴师问罪,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太后并未责罚他。
&esp;&esp;太后只是问他:“望舒,你到底为何要囚王燃犀?吾可不信,她什么图谋不轨之处。”
&esp;&esp;崔珣敛眸答道:“臣抓王燃犀,并非因她图谋不轨,而是她丈夫裴观岳只知圣人,不知太后,臣想杀杀他的气焰,但没想到察事厅意外失火,害了王燃犀性命。”
&esp;&esp;珠帘后,太后轻笑一声,她直视着崔珣:“当真?”
&esp;&esp;“千真万确。”崔珣垂首:“臣的身家性命,都源于太后,所做之事,也都只会为太后筹谋。”
&esp;&esp;崔珣的这句话,显然正中太后下怀,她笑了一笑:“今日天气不错,望舒,你伴吾去太液池走走吧。”
&esp;&esp;太液池位于大明宫禁苑,春日时分,太掖池碧波微漾,绿柳垂丝,莺啼蝶飞,崔珣伴于太后左右,于池边游览,一阵春风吹过,身着深绯官服的崔珣忍不住掩袖咳嗽,太后见状,唤内侍取来雪白狐裘,披于崔珣身上。
&esp;&esp;崔珣谢恩之后,太后才道:“你这病,让御医瞧过没有?”
&esp;&esp;崔珣道:“瞧过了,也开了方子。”
&esp;&esp;太后点头:“那些弹劾你的奏表,你也不需忧心,有吾在,圣人也不敢发作你。”
&esp;&esp;“谢太后。”
&esp;&esp;“裴观岳等人,心心念念,要将吾赶去兴庆宫养老,但吾不会趁他们的心,否则,三十年心血,会付之一炬。”
&esp;&esp;崔珣恭敬道:“臣愿做太后手中的刀。”
&esp;&esp;“三年前,你在大理寺的监狱里,也跟吾说这句话。”太后似是想到当日那个生于绮罗、长于珠玉,本应泛舟曲江,听雨品茗的博陵崔氏子,却在阴暗囚牢中,拖着遍体刑伤的身躯爬向她,用被拔光指甲血淋淋的十指抓着她的裙摆奄奄一息恳求,她徐徐道:“否则,就凭你出自博陵崔氏,吾就不可能用你。”
&esp;&esp;太后对博陵崔氏的憎恶,向来毫不掩饰,先帝驾崩后,太后临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尚书右仆射崔颂清赶出长安,崔颂清辅助先帝推行太昌新政,劳苦功高,能力卓绝,但太后执政的这二十年,他却始终闲居博陵,连个江州司马都没得做。
&esp;&esp;没有人知道太后为何这么憎恶博陵崔氏,许是太昌帝修《宗族志》一书,群臣将博陵崔氏排在李氏皇族之前的旧怨,又或许是崔颂清为相的时候与太后有了矛盾,总之,太后临朝以来,没有用博陵崔氏一人。
&esp;&esp;直到崔珣出现。
&esp;&esp;太液池侧,杨柳青青,崔珣裹着雪白狐裘,身影清雅如玉,与绿柳一起倒映在碧波之中,显得他像一个抚琴观鹤、淡泊名利的世家贵胄,但谁能想象到,此人非但不淡泊名利,而且心狠手辣,恶行昭彰,根本是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的活阎王。
&esp;&esp;他垂首道:“太后救了臣的性命,臣愿为太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