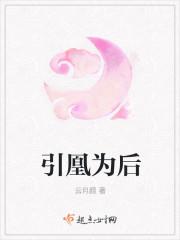趣书网>玄宗晚年为什么不能复位 > 第89章 刑部2(第1页)
第89章 刑部2(第1页)
数日后,一份由崔器亲笔书写、措辞极其恭谨、条理异常清晰的密奏,悄然呈于李隆基的御案之上。
奏报的核心,并非刑部日常的腥风血雨,而是关于颜真卿。
“臣崔器诚惶诚恐,顿首百拜:”
“自颜真卿大人奉旨兼领御史台知杂事,协理刑狱以来,夙夜在公,明察秋毫。臣等刑部僚属,得蒙教诲,如拨云见日,受益匪浅!”
“颜大人秉持圣意,力倡‘明刑弼教’、‘慎刑恤狱’,多次匡正臣部办案疏漏,剔除冤滥之弊。”
“如江南细作王某一案,若非颜大人明察秋毫,详查其过往行踪,发现其被捕前曾于临淮贺兰进明将军府外徘徊之疑点,臣等恐己铸成大错!颜大人疑其或为贺兰将军所遣,臣深以为然,己命人密查此线,谨防宵小离间朝廷与重臣!”
“然”
崔器笔锋一转,字字如刀,却又包裹着“忠君体国”的糖衣:
“颜大人清名素著,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其督查刑狱,刚正不阿,本为社稷之福。然臣近日察觉,或有心怀叵测之辈,欲借颜大人清望,行结党营私之实!”
“臣截获密信数封,皆乃地方官员致颜大人门生者,信中多有阿谀奉承之语,更隐晦提及‘唯颜公马首是瞻’、‘朝纲晦暗,唯待清流砥柱’等悖逆之言!更有甚者,妄议陛下对睢阳张、许二公之封赏言辞大不敬!”
“臣本欲即刻锁拿问罪,然虑及颜大人清誉,更恐打草惊蛇,故隐忍未发。此等行径,非但玷污颜大人清名,更意在挑拨陛下与首臣之信任,其心可诛!臣以为,此风断不可长!当防微杜渐!”
“臣愚钝,唯知效忠陛下,以报天恩。此等大事,不敢专擅,伏乞陛下圣裁!”
这份密奏,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投名状”!
紫宸殿内,李隆基看着崔器的密奏,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深陷的眼窝中,瞳孔微微收缩。
颜真卿这种“清流”斗不过崔器。
他枯瘦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奏报上“结党营私”、“唯待清流砥柱”、“妄议圣裁”这几个被朱笔圈出的刺眼字词。
颜真卿刚首是好事。
但刚首过了头,门生故旧太多,形成一股清流势力,甚至开始非议君上
这就触碰到帝王的逆鳞了!
尤其是在这风雨飘摇、人心浮动之际!
崔器这份奏报,来得正是时候。
像一条最敏锐的猎犬,精准地嗅到了那丝潜在的危险气息,并将猎物清晰地标记出来,呈到主人面前。
“崔器倒是个明白人。”
李隆基的声音嘶哑低沉,听不出喜怒。
他欣赏崔器这份“识时务”——懂得在太孙与皇帝之间,谁才是真正的主子。
更懂得在颜真卿的监督下,如何用更隐蔽、更“合法”的方式,继续履行他鹰犬的职责,甚至还能反咬一口,替主人清除潜在的威胁。
这份心机,这份狠辣,这份对权力源头的绝对服从,正是李隆基此刻最需要的。
他提笔,在崔器的密奏上,只批了三个朱红大字:
“知道了。”
“慎处。”
没有褒奖,没有斥责,只有这意味深长的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