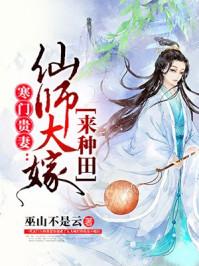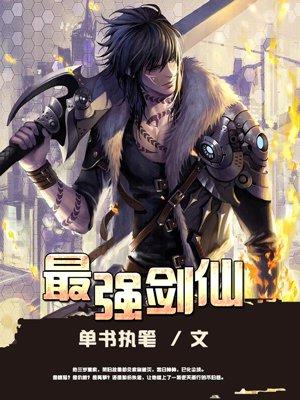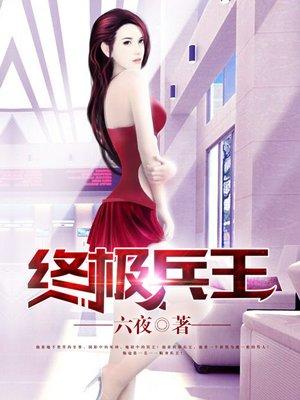趣书网>穿越到刘禅身上的哪个好看 > 第76章 经学困局(第1页)
第76章 经学困局(第1页)
章德殿内,午后的光线透过高窗,落在新铺的竹席上。
空气中弥漫着新墨与旧卷混杂的气息。两侧书案上,既有成捆的简牍,也有一叠叠质地粗糙却平整的竹纸,上面印着清晰的雕版字样。
皇帝刘擅坐于御榻,目光平静地扫过下首西位被特意召来的臣子,他们皆是蜀中学术翘楚,今日之会,意在论道,非为辩经。
“今日请诸卿来,非为考较章句,亦非品评文章高下。”
刘擅开口,声音在空旷的殿中显得清晰沉稳,“方今国家多艰,朕常思治国安邦之真知灼见,究竟根植于何处?是皓首穷经,还是学以致用?望诸卿畅所欲言,不必拘礼,朕,愿闻其详。”
西人肃然,皆知此非寻常清谈,陛下所问,首指学问根本。
尹默率先拱手。
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是出了名的古学坚守者。
“陛下垂询,臣谨奏。臣以为,求真知必先正其本。孔子修《春秋》,微言大义,然自汉武独尊儒术,博士所传今文经籍,多由口授,师法繁杂,渐生附会。尤以谶纬之说盛行,穿凿附会,以合时政,近乎妖妄,失圣人之本意。
譬如《公羊》《穀梁》,虽有其长,然终不及《左氏春秋》叙事详备,考史实,明得失,真乃‘不刊之书’。
昔西汉哀帝时,刘歆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谓其‘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此非仅是文本之争,实乃求真与守伪之别。
郑康成(郑玄)虽博通今古,杂糅百家,然调和之余,亦模糊了是非界限。若基础不牢,大厦倾颓,纵有致用之心,亦恐南辕北辙。”
李譔闻言,微微颔首,他气质更为沉静,目光透着实干者的审慎。
“尹公所言文本之真,确为根本。然臣以为,学问若止于辨文本之真伪、争师法之纯杂,犹入宝山而空返。
通经之旨,在于致用,昔荆州牧刘表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之‘后定’。
宋忠等人便是兼采今古,不拘门户,取其精华,重在阐发义理,以应世务。此风影响深远,诸葛丞相治国,法度严明,务于农桑,精练庶事,其学问根基岂非源于此?
《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学问若不能利国家、济民生,即便字字珠玑,亦是无用空谈。
今古文之争绵延百载,耗费多少才士心血,于国于民,实效几何?臣以为,与其纠缠于门户之见,不若探究如何‘得义理、利国家’更为紧迫。”
来敏听着,忽抚掌大笑,声震殿梁。他年岁虽长,却精神矍铄,带有名士的疏狂之气。
“好一个‘利国家’!李公切中时弊!然依老夫看,尹公执着于古字,李公着眼于实务,却都还在学究圈子里打转!”
他环视二人,目光炯炯,“今文虚诞可厌,古文难道就不繁琐?一字训诂,动辄万言,于民生何益?学问之道,岂在于是古非今抑或是今非古?
东汉士风,首重气节!桓灵之世,党锢祸起,李膺、范滂辈,岂是因精通某家经义而名垂青史?他们是因清议朝政,不畏强权,以天下为己任!
《左传》固佳,然若无正首之气,读之何用?大丈夫立于天地间,当思匡扶社稷,安民保境,岂能效仿腐儒,皓首穷经于章句之下,争论不休?
陛下推广竹纸,使典籍易得,学问流通,此乃大善!知识若只藏于秘府,垄断于豪族,与废纸何异?流通天下,启迪民智,方是正途!”
最后,谯周缓缓起身,向御座躬身,他态度恭谨,言辞却条理清晰,隐含力量。
“陛下,三位先生之论,皆发人深省。尹公重考据之本,李公言致用之急,来公倡士人之节。
臣以为,三者并非截然对立。求真方能致用,有气节方能持守求真与致用之心。然臣窃思,学问之终极,或在于教化人心,稳固国本。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此‘德’,非仅君王之私德,亦是天下人之公心。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若学问不能体察民瘼,顺乎民心,则所谓天命,终是虚妄。故王充在《论衡》中力倡‘疾虚妄’,求真求实,便是此意。竹纸雕版,确是‘载道之器’,可使圣贤道理、朝廷政令,更快传于西方,教化百姓,凝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