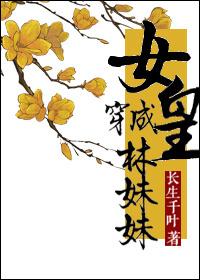趣书网>小作精又在生气了by小作精笔趣阁 > 第16章(第3页)
第16章(第3页)
乐澄恼羞成怒,正准备脱鞋的动作顿住,脸一红:“……都哪一年的老黄历了?还提。”
“半年零十五天。”
傅时勋冷冷地报出精准时间。
是俩人闹分手的前夕,所以傅时勋记忆犹新。
那天他刚出差回来,刚想推门而进,结果才迈出一只左脚,啪!一个玻璃杯砸在他的脚边。
“谁准你进门先跨左脚的?”
乐澄的哭闹声下一秒传到他耳边。
加班了几乎三天两宿没合眼的傅时勋当场来了脾气。
好哇,他在外工作当牛做马。
就这样也没忘记见缝插针去巴黎给老婆买包。
结果一见面老婆砸他,还因为进门先伸哪只脚这么离谱的理由生他的气。
傅时勋气得想立刻把这个爱作的小东西狠狠做一顿。
做完就老实了。
结果一低头。
他看到地毯上散落的玻璃碎片。
透明的玻璃碎片大片大片四散而开,上头有不少染上了洇红的血迹。
而玻璃碎片的中央。
乐澄苍白着一张小脸,红着眼睛,没穿袜子,也没穿鞋。
……后来医生从乐澄的脚掌上足足捏出来十八块儿小玻璃碎片。
那些碎片拼凑起来可能还不到一个大拇指甲盖那么大。
却叫乐澄吃尽了苦头。
连输液都害怕的不得了的人,那天被医生拿着镊子在脚上血肉模糊的翻找了一个多小时,哭到眼泪都已经干了,嗓子也哑了。
傅时勋又是气又是心疼。
气他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心疼他受了疼也受了委屈。
尤其是他后来从医生口中得知,虽然医生已经用尽各种方法把玻璃渣从乐澄的脚上挑出来,甚至用上了显微镜。
然而一些肉眼不可见的极细玻璃纤维,仍是无法被发现。
它们会顺着伤口进入乐澄的血管,在他的血液中流淌,也许这辈子都留在丢在乐澄的身体里。
那天后傅时勋扔掉了家里所有玻璃杯。
可却忘了,公司里还有。
更何况,他再神通广大,总不可能扔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玻璃杯。
一想到这个事实,傅时勋眼神微不可见暗了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