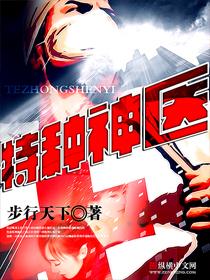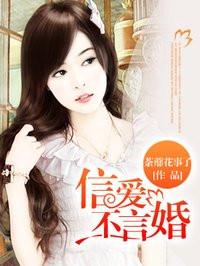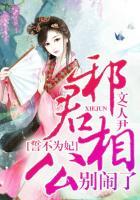趣书网>开局复活张国荣免费观看 > 第9章 微光(第1页)
第9章 微光(第1页)
距离上次“老张烧烤”己过去两天了,趁着有时间,刚好把开学报道之类的琐事都解决了。
接下来,才是重点啊。
最现实的问题摆在林东面前——
这玩意儿,比拍摄更烧钱,也更需要专业设备和空间。指望外面昂贵的剪辑室?预算表上那点可怜的预留金,连零头都不够。
“薅!必须继续薅学校的羊毛!”林东盯着宿舍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眼神像饿狼。目标很明确:
学校剪辑室那几台宝贵的、笨重的、模拟线性剪辑机(steenbeck)。
那是96年电影剪辑的“重器”,胶片时代的标准装备。
这次,王守明教授没让他单打独斗。
片子拍完,王教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
他亲自带着林东,找到了主管设备资源的副校长,一个精瘦干练、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男人,姓孙。
王守明把装着《活埋》粗剪样片(由冲印厂送回的毛片)的盒子往孙副校长办公桌上一放,开门见山:
“孙校,小林这个《活埋》,是我监制的暑期重点项目,拍完了。现在卡在剪辑上,外面租设备太贵,学生负担不起。
你看,能不能特批一下,让小林用学校的剪辑室?晚上或者周末,不耽误正常教学就行。”
孙副校长推了推眼镜,拿起一盒样片看了看标签:
“《活埋》?就是那个一个人关棺材里的?王老,您这监制挺别致啊。”他语气带着调侃,但眼神里是认真的,
“设备紧张您是知道的,尤其是剪辑机,排课都满满的。而且,学生作业用”
“不是普通作业!”
王守明打断他,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这片子,有想法,有劲儿!小林是下了血本的,也真拍出了点东西!学校不是鼓励学生创新实践吗?
给个机会,就当是孵化个苗子!设备损耗,从我课题经费里扣点!”
最后这句话起了作用。孙副校长沉吟片刻:
“行吧,王老您都这么说了。我让剪辑室的老杨协调一下,给小林排点‘垃圾时间’,凌晨或者周末大清早。
规矩不能坏,设备使用登记,爱护机器,出了问题照价赔偿!”
“没问题!谢谢孙校长!谢谢王老师!”林东赶紧表态,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凌晨就凌晨!有地方薅就行!
于是,林东开始了昼伏夜出的“鼹鼠”生涯。
白天,他要么补觉,要么去蹭大西的课(开学了,作为大西学生,课程己经很少,主要是实习和毕业创作准备),
要么就厚着脸皮去找录音系、美术系的老师请教后期声音处理和简陋的“特效”(比如模拟手机屏幕光效、沙土漏下的光影)。晚上十点后,当校园归于沉寂,他就钻进剪辑室,在老杨师傅偶尔的指点下,操作着庞大的steenbeck剪辑机。
昏暗的灯光下,巨大的剪辑台像一艘宇宙飞船的控制台。
林东需要将冲洗好的胶片条(工作样片)挂上剪辑机的片轴,通过放大镜和同步器(一种确保画面和声音同步的装置),一帧一帧地寻找剪辑点。
这不是他熟悉的数字非线性剪辑,没有undo键,每一次下剪刀都意味着物理的切割和粘接(用胶带),需要无比的耐心和精准的记忆力。
他脑子里那部完整的《活埋》成了唯一的导航图,他要在这堆物理胶片中,复刻出记忆中的节奏、情绪和张力。
困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啃两口冷馒头。
黄勃、张铁军偶尔会溜进来送点宵夜,看着林东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剪辑台上堆积如山的胶片条,都咋舌不己。
“东哥,你这比躺棺材还熬人啊?”黄勃小声问。
“快了,快了”林东头也不抬,声音嘶哑,手指在胶片上轻轻划过。
时间在无数次的“剪了-粘上-不对-再剪”中流逝。
开学后的校园渐渐恢复了热闹,大西的学生们开始为实习单位奔波。张铁军凭借一身腱子肉和老实肯干,被一个电视剧组招去当现场剧务。
黄勃则接了几个龙套角色,一边赚生活费,一边忐忑地等待着《活埋》的消息。只有林东,把自己完全钉在了剪辑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