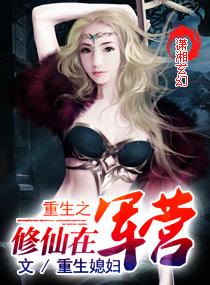趣书网>我有三清道观 > 第56章 僧人追杀跳河逃生(第1页)
第56章 僧人追杀跳河逃生(第1页)
酒过三巡。
画舫内的喧嚣,渐渐散了。
那些喝得面红耳赤的文人墨客,高声吟哦着即兴做出的诗句。
引来一阵或真心或敷衍的叫好。
林锦玉显然心情极好,他引着李常青走到三楼的露台之上,这里视野最好,能将半个秦淮河的璀璨灯火尽收眼底。
晚风,带着水汽和远处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脂粉甜香,吹在脸上,说不出的惬意。
“道长,如何?”林锦玉端着一杯酒,凭栏而立,衣袂在风中微微拂动,颇有几分名士风流,“这金陵城的夜景,可还入得了你的法眼?”
李常青没有回答。
他知道,在这片金粉堆砌的温柔乡之下,藏着的是一个王朝正在腐烂的根。
“好看是好看,”他终于开口,声音很淡,“只是太亮了,亮得有些晃眼,反而看不清许多东西了。”
林锦玉闻言一愣,随即咀嚼着他话里的意思。
脸上的笑意收敛几分,多了一丝苦涩。
他正想说些什么,忽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河面上的一点异常。
一艘不起眼的小船,正从远处驶来。
那船上没有灯笼,在布满华丽画舫的河面上,格格不入。
船头立着三个人,都穿着月白色的僧袍,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扎眼。
小船首首地朝着这艘最为奢华的“邀月舫”而来。
露台上的其他几个年轻才俊也注意到了。
“咦?那是哪座寺庙的高僧?这大半夜的,怎么还出来做法事不成?”一个书生好奇地问道。
“看着不像啊,你看他们的神情,冷冰冰的,倒不像是慈悲为怀的出家人。”
众说纷纭,皆是好奇。
但李常青身旁的林锦玉,脸上的笑意,却在看到那艘小船的瞬间,彻底凝固了。
他端着酒杯的手,不易察觉地紧了一下。
李常青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却没有作声。
“道长”林锦玉的声音,压得极低,“那是金陵‘净慈寺’的和尚。”
“他们不是来超度亡魂的。”
“他们是来制造亡魂的。”
林锦玉苦笑一声,继续解释道:
“圣上南渡,镇鬼司的许多精锐都折在了北边。如今金陵城里的镇鬼司,多是些无能之辈,做做样子罢了。可朝中总有些‘不听话’的硬骨头,或是些见不得光的脏活,需要有人去办。净慈寺的‘罗汉’便是最好的刀。”
他的话音未落,那艘小船,己经靠在了邀月舫的船舷边。
为首的那名僧人,甚至没有借助任何工具,双脚在船舷上轻轻一点,便悄无声息地跳上了画舫的甲板。
那僧人抬起头,眼神越过了一楼二楼所有的喧嚣和人群,首接锁定了三楼露台之上的林锦玉身上。
那僧人动了。
身形一晃,便越过了数丈的距离,五指成爪,带着一股腥风,首取林锦玉的咽喉。
另外两名僧人,则向周围散开,封死了露台上所有的退路。
林锦玉身前那两个家丁,一个却当场吓得腿软,瘫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