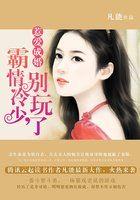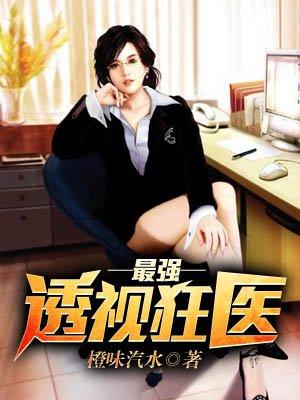趣书网>医圣传筋骨贴是正规品牌吗 > 第390集 苗医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第2页)
第390集 苗医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第2页)
基金的另一笔重要支出,是开办“苗医传承班”。招生启事贴出去那天,蒙松以为最多能来十几个年轻人,没想到来了三十多个,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在外打工回来的苗族姑娘,甚至还有个金发碧眼的美国留学生。
“我叫安娜,在哈佛学人类学。”女孩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我奶奶得了帕金森,是苗医的针灸减轻了她的手抖——我想知道为什么。”
传承班的课堂设在新修的文化站里,墙上挂着蒙松和其他老苗医的照片。第一节课,蒙松没讲药理,而是带着学生去后山采药。他指着一株开着紫花的植物说:“这是‘紫菀’,要在露水干了之后采,不然药性会随露水走。”
阿依蹲在旁边做笔记,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动。蒙松看出她的犹豫:“想问什么?”
“师父,书上说紫菀要晒干,可您上次给王阿婆治病,用的是新鲜的。”
“傻丫头。”蒙松笑了,“王阿婆肺虚,新鲜的紫菀带水汽,能润喉;要是治咳嗽带痰,就得晒干了用——苗医治病,从来不是死搬方子。”
安娜举着录音笔,把这段话记了下来。她后来在论文里写道:“苗医的智慧不在书本里,而在山间的晨露里,在病人的呼吸里。”
传承班最特别的课程是“苗医音乐疗法”。寨子里的老歌手教学生唱采药歌,那些没有歌词的调子像山风拂过竹林,能让人不自觉地平静下来。有次安娜试着用吉他弹这段旋律,蒙松听了直点头:“只要能让人舒服,用什么乐器都行。”
年底的汇报演出上,学生们表演了“银针刺绣”——一边唱着古老的歌谣,一边在布帛上用银针绣出穴位图。台下的观众里,有当年捐款的老太太,有“百草集”的张敏,还有省文化厅的领导。当阿依用苗语念出《苗岭百草经》的开篇时,蒙松忽然觉得,那些曾经让他夜不能寐的担忧,都化作了台上的光。
四、基地扎根
苗医文化传承基地的奠基仪式定在春分那天。蒙松带着学生们在地基上撒了一把药草种子——有艾草、薄荷、金银花,都是苗医常用的药材。“让它们陪着基地长。”他说。
基地的设计图改了七遍。最初的方案是现代化的展览馆,蒙松看了直摇头:“苗医不是摆着看的,得能看病、能制药才行。”最后定稿的图纸里,有诊室、药房、炮制坊,还有一片仿野生的药圃。
建设期间,工人们总能在工地上发现惊喜。挖地基时挖出了清代的药罐,砌墙时找到刻着草药图案的砖块——原来这片土地早就记得苗医的故事。张敏听说后,特意让人把这些“宝贝”做成了展柜,摆在基地的入口处。
最热闹的是炮制坊。老苗医们带着学生用古法炮制药材:把当归埋在米里炒,让杜仲在火上冒白烟,将天麻泡在米酒里发酵。香气飘出基地,引得寨子里的孩子天天来门口等着,盼着能分到一片蜜炙的甘草。
基地落成那天,来了很多人。蒙松穿着新做的苗服,胸前挂着师父传给他的银药铃。当他揭开“苗医文化传承基地”的牌匾时,铃铛发出清脆的响声,惊起了药圃里的一群蝴蝶。
李教授拉着蒙松的手,指着电子屏上滚动的数字:“基金已经筹到三千多万了,还在增加。”蒙松没说话,只是看着药圃里的幼苗——那些春分种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子。
晚上的篝火晚会上,安娜弹着吉他,阿依唱着采药歌,张敏跟着节奏拍手。蒙松坐在老人们中间,喝着自家酿的米酒,忽然听见有人喊他。是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举着本彩色画册:“蒙爷爷,这是我画的苗医故事,能给我签个名吗?”
画册上,一个穿苗服的老人正给病人针灸,旁边的药圃里开满了花。蒙松接过笔,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又画了一株小小的七叶一枝花。
他想起很多年前,师父也是这样教他认药草的。那时的苗岭,风里飘着药香,歌里藏着药方,就像现在这样。
尾声
五年后,蒙松的头发全白了,但他依然每天去基地坐诊。阿依成了传承班的老师,教学生们辨认草药时,语气像极了当年的蒙松。安娜留在了苗寨,她翻译的《苗岭百草经》英文版在国外出版,扉页上印着蒙松和药圃的照片。
基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不断更新的地图,上面标注着新发现的古籍、新增的传承人、新建的苗医诊所。李教授每次来都要站着看很久,他知道,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都是苗医文化重新扎根的地方。
有天蒙松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本精装的书,作者是那个寄硬币的小学生。书里写着他和苗医的故事,最后一页画着一个基金的标志,旁边写着:“原来很多人一起使劲,就能留住想留住的东西。”
窗外的药圃里,七叶一枝花已经开了,七片绿叶托着一朵洁白的花,像极了阿依当年的绣片。蒙松拿起桌上的《苗岭百草经》,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书页上,那些曾经脆弱的字迹,此刻正散发着安稳的光。
他知道,苗医的故事还很长。那些藏在古籍里的智慧,那些留在歌声里的药方,那些握在传人手里的银针,会像苗岭的草木一样,在时光里生生不息。而那笔汇聚了无数善意的基金,就像山间的清泉,滋养着这一切,让药香永远飘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