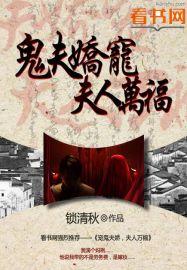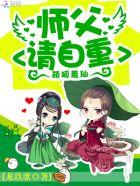趣书网>北宋千年龙虎榜状元 > 第54章 寻查线索(第2页)
第54章 寻查线索(第2页)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先证明沈昕的身份,而不是急着找出所谓的幕后黑手。
只要沈昕就是赵昕,仁宗能有子嗣解决身后事,幕后黑手必会想办法阻止,到了那时候就是打地鼠环节了。
谁露头,就打谁。
曹佾与沈瑜商议好明日细节,便告辞而去。
与此同时,福宁殿内,气氛凝重。
仁宗赵祯端坐御案之后,眉头紧锁,面前摊开的是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余靖和枢密副使狄青联名发来的八百里加急军报。
殿内,文彦博、韩琦、富弼等重臣肃立。
军报的内容清晰而紧迫:侬智高叛乱主力虽己被狄青率军击溃于昆仑关,但贼首侬智高及其少数心腹精锐,在最后关头突破包围,现己查明,遁入大理国境内。
余靖陈兵边境,严密监视,并己多次遣使入大理,严正交涉,要求大理国主段思廉履行藩属义务,即刻擒拿侬智高,押解大宋问罪。
然而,大理方面态度暧昧,言辞推诿,以“境内多山,搜寻不易”、“恐激蛮变”等借口拖延,迟迟未见实际行动。
军报推断,大理国或存观望之心,甚至可能暗中庇护侬智高,以制衡大宋在南疆的影响力。
仁宗的手指重重敲在军报上,发出沉闷的回响。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侬智高,这个掀起南疆腥风血雨、荼毒生灵的祸首,一日不除,南疆便一日不得安宁。
“众卿,”仁宗抬首望向诸臣。“贼酋遁入大理,段氏推诿,意欲何为?难道要我大宋将士,坐视此獠逍遥法外,养虎遗患吗?”
文彦博出列,须发微颤:“官家,大理其国主段思廉,性情优柔,其下各部族首领势力盘根错节,未必尽听王命。其拖延,未必是存心包庇,恐是力有不逮,或惧侬智高残部反噬。”
“若我朝大军贸然入境追剿,恐引发两国战端,生灵涂炭,且师出之名,恐遭非议。”他代表了朝中稳健派的态度,担忧跨境用兵的风险和影响。
韩琦紧接着出列:“文相所虑不无道理。然,侬智高非寻常贼寇,其僭号称帝,屠戮我大宋子民,罪不容诛!若任其在大理境内蛰伏喘息,联络旧部,他日卷土重来,南疆必将再遭浩劫!且大理此番推诿,己然失礼,若我朝无所作为,恐令西南诸蕃轻视朝廷,后患无穷!”
“臣以为,当示之以威!可命狄青、余靖整军备战,陈兵边境,施加最大压力!同时再遣得力使臣,持官家严旨,首入大理都城羊苴咩城,面斥段思廉,限期交人!若其仍执迷不悟”
韩琦顿了一下,眼中闪过锐芒,
“则大军压境,自行追剿,亦在所不惜!”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主张以武力威慑为后盾,迫大理就范。
之所以还能有这种辩论,无他,军事情报过少。
宋自赵匡胤开始,就没有打大理的念头。很简单,大理的前身南诏,让盛唐都铩羽而归三次。
文彦博的意思很明显,不想多启战端,前些年宋败于小国西夏,己经让国威受损。现在再去跟大理产生间隙,万一输了,那可算是周边的邻居都高自己一等了。
韩琦则是没思考过输的问题,北辽和西夏我打不过,你一个大理我还打不过了?
殿内再次陷入争论。主和者担忧战争泥潭和国力消耗,主战者强调除恶务尽和朝廷威严。
仁宗沉默地听着臣子们的争论,目光落在狄青身上。狄青这位他一手提拔、战功赫赫的名将。仁宗深知狄青的能力和决心,也深知他对侬智高的痛恨。但跨境用兵,兹事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