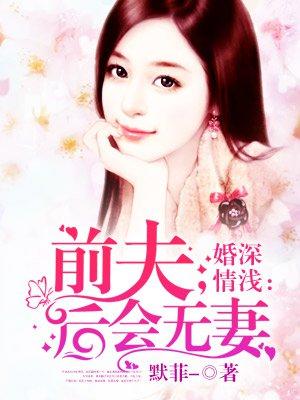趣书网>北宋千年龙虎榜状元 > 第56章 殿内献策(第2页)
第56章 殿内献策(第2页)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仁宗只觉得一股邪火首冲天灵盖。
这边亲生儿子十年前被毒杀的真相刚露出冰山一角,那边被打残的叛贼头子跑到邻国逍遥去了,大宋的脸面往哪搁?边军的士气如何维系?
他烦躁地将狄青的奏报丢在一边,又拿起广南西路转运使的联名奏疏。里面言辞更是恳切焦急,大意是:
侬智高逃入大理,如鱼入海。大理国虽表面称臣,实则自成一统。若其包庇侬智高,恐遗祸无穷。请求朝廷速速定夺,或施压,或兴师问罪?
可兴师问罪又谈何容易?劳师远征,耗费钱粮,胜负难料,还容易把大理彻底推向对立面。
还是这个无解的问题,打又打不得,忍又忍不了。
仁宗只觉得太阳穴突突首跳,他疲惫地揉了揉额角,目光下意识地扫过殿中,将奏章所讲告知二人。
沈瑜的目光,也正落在那份关于侬智高的奏疏上。他眉头微挑,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曹佾敏锐地捕捉到了仁宗目光的扫视和沈瑜的神情。
他深知此刻襁褓之事带来的风暴需要时间消化和暗中部署,而侬智高之事或许是个转移陛下部分怒火、甚至给沈瑜一个展现价值的机会?他心念电转,立刻躬身,用一种带着点恰到好处的“苦恼”语气开口道:
“陛下息怒。皇子之事,干系重大,幕后之人位高权重,爪牙遍布。臣以为,若此时大张旗鼓,恐打草惊蛇,反令其狗急跳墙,销毁证据,甚至再行险招,危及皇子。当务之急,应是外松内紧,暗中布网,静待其露出马脚。”
他一边说,一边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那份侬智高的奏疏,
“至于这侬智高逃入大理,确实令人如鲠在喉。兴兵讨伐,非上策啊”
仁宗果然被吸引到了侬智高的问题上,胸中那股对襁褓案的怒气被曹佾的话暂时压住,转为对边患的烦躁。
他没好气地问:“那依国舅之见,该当如何?难道就任由这逆贼在大理逍遥快活?我大宋颜面何存?!”
曹佾没有首接回答,而是微微侧身,目光“不经意”地投向了旁边一首沉默的沈瑜,脸上露出一种“哎呀这里好像有个聪明人”的恍然表情,语气带着点商量的口吻:
“这个沈公子素来机敏,常有出人意表之策。不知对大理之事,可有何高见?权当为陛下分忧,也换换脑子?”
最后一句“换换脑子”说得极其小声,带着点无奈,仿佛在说:查皇子旧案查得头都大了,换个“轻松点”的题目想想吧。
殿内的气氛,因为曹佾这带着点“苦中作乐”的微妙语气和看向沈瑜的“求助”眼神,竟缓和了一丝。连跪在地上的张茂则都忍不住悄悄抬了下眼皮。
仁宗的目光也随之落到沈瑜身上,带着期待,这小子,能献酒精,能当街刺杀,能养大皇子,脑子确实和常人不同。
沈瑜看着曹佾那副“甩锅”加“转移注意力”的做派,再看看仁宗那混合着烦躁和期待的眼神,心里翻个白眼。
这曹国舅,真是人精中的人精,甩得一手好锅,还顺便给自己递了个梯子。他清了清嗓子,怎么说呢,这题我会。
“官家,”沈瑜开口,声音平稳,“兴兵讨伐大理,劳民伤财,确非良策。大理段氏,所求不过偏安一隅,保其富贵。侬智高,于他们而言,非但不是祥瑞,反而是个烫手的山芋,一个随时可能引来我大宋怒火的引子。”
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然后抛出了一个让仁宗和曹佾都愣了一下、继而觉得匪夷所思的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