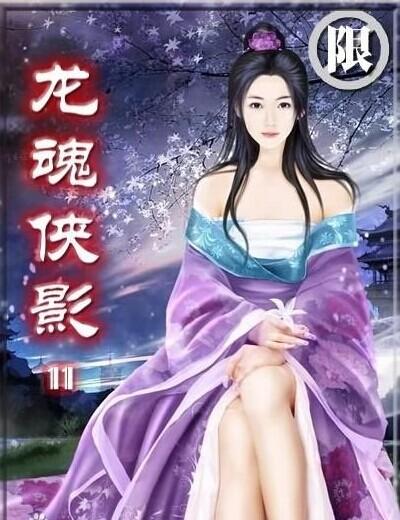趣书网>清流党 严党 > 第370章 考官篇四(第2页)
第370章 考官篇四(第2页)
赵文华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如同被冻住的猪油。
他张着嘴,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周围的几位考官都注意到了这无声的尴尬,有人低头装作看卷,有人嘴角微微抽动。
赵文华老脸一红,最终只得冷哼一声,讪讪地踱回自己的座位,那背影僵硬得如同生锈的铁板。
陈恪根本不在意身后那道怨毒的目光。他的心神已被手中的新卷吸引。
这份策论开头便与众不同。
它没有急于站队抨击或鼓吹海禁,而是如同一位沉稳的史家,从上古“市易有无”讲起,历数商周、秦汉、隋唐、宋元的海路贸易兴衰,条分缕析地阐述开放与封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弊得失。
论据扎实,文气平和,逻辑清晰。
最后,文章竟以极其标准的“颂圣”结尾:“伏惟陛下天纵圣明,洞察幽微,于海疆之策,自有乾纲独断。臣等惟恪遵圣谕,竭诚效力而已。”
陈恪的嘴角,难以抑制地向上扬起。
这手法……太熟悉了!
这不正是他当年中举时写《盐铁论》策论的翻版吗?
只不过此人比他当年更加圆融、更加稳妥,那份锐利的锋芒被厚重的史料包裹,最终以恭谨的马屁完美收束,堪称考场“保命”与“展才”的典范。
“好一个‘述而不作’!”陈恪心中暗赞,这种写法,在嘉靖这种喜欢掌控一切的帝王眼中,或许比那些锋芒毕露的激进言论更易被接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他提起朱笔,在卷头工整地批下一个醒目的“甲上”,并写下评语:“条陈古今,洞悉利害,立论持中,文理俱优。”
这份卷子,正是陈谨所答。
时间在笔尖沙沙声中流逝。
陈恪又遇到了几份让他眼前一亮的卷子。
一份卷子,字里行间透着刚直与忧虑。
它大胆抨击当下海禁政策的弊端——官商勾结、禁令形同虚设、沿海民生凋敝、卫所糜烂无力抗倭。
但同时,它并非一味否定,而是在痛陈之后,隐隐流露出“穷则变、变则通”的求变之意,提出“严查私贩,重振武备,以威立禁”或“于闽粤择良港,设市舶司严管,以疏代堵”的初步设想。
虽然具体措施仍显粗糙,但其间的忧国忧民之思与一丝不囿于陈规的灵气,让陈恪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海青天”的影子。
他对海瑞那种近乎偏执的刚直并非全然认同,但那份为民请命、不畏权贵的赤诚风骨,他始终心存敬意。这份卷子,他同样批了“甲上”,评曰:“痛陈时弊,忠直敢言,亦有变通之思。”
而这正是温应禄的文章。
另一份卷子则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力与改革热情。
作者以宏阔的视野,描绘了开海通商后万国来朝、货殖繁盛的景象,甚至提出“以商利养水师,以水师护商道”的构想,隐隐触及了海权思想的边缘。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未知海洋的向往和对未来的乐观预言。
陈恪细读之下,推测作者可能是沿海人士,见闻使然。
他欣赏这份超越时代的见识,但也深知在此时的大明,这样的蓝图需要何等能力与魄力的人才能支撑。
他批了“甲中上”,评曰:“视野宏阔,具前瞻之识,然实施之艰,犹待深虑。”
这无疑是梁梦龙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