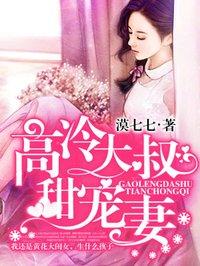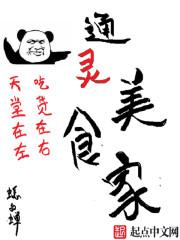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24章 大宋之耻(第2页)
第24章 大宋之耻(第2页)
“臣宗泽——”
“臣李纲——”
“叩见陛下。”
赵恒淡声道:“二位卿家平身。”
宗泽目光沉凝,李纲却已有些迫不及待,拱手上前一步,激动道。
“启禀陛下,韩将军已顺利抵达建康!诸军士气旺盛,当地守备稳定,选址之事已有雏形,行宫亦在加紧修缮,至多半月可成!”
赵恒眉梢微挑,略一点头。
“陛下,韩将军传言,所求不多,只盼陛下亲临,得百姓所望,固我大宋根本。”
李纲说着,面色微红,眼神炽热。
宗泽却始终低头不语,似乎在权衡什么。
赵恒缓缓起身,走下了御阶,开口道:“迁都之事不必张扬,一切从简即可,宫殿什么都不要大肆铺张。”
李纲闻言,肃然拱手:“陛下高义!微臣佩服!韩将军亦言,建康之民见宋军旗帜,夹道相迎,百姓呼声震耳!多有老卒带头重披旧甲,少年自发参军,恨不得即刻北伐雪耻!”
宗泽沉吟片刻,忽然抬头道:“启禀陛下,臣近日密奏未呈,便借今日面君,直言不讳。”
赵恒轻轻点头:“宗大人但说无妨。”
宗泽目光炯炯,带着一丝掩不住的激昂,道:“如今民间义军蜂起,旧部残卒纷纷来归,皆言愿听朝廷节制,重整军马抗金!臣亲自前往整编五州义军,士气极盛,不逊官军!”
“其中更有民间义士,家破人亡后,募资建营,投效前线!”
“陛下!”宗泽重重叩首,声音一震,“大宋之心,未死!”
赵恒一怔,眸中掠过一抹意外,但随即轻轻一笑。
“好。”他低声道,“你说这话,朕爱听。”
他话锋一转,话音骤冷:
“可惜,朝中那些穿蟒袍、戴乌纱的未必个个都有此志。”
宗泽闻言,神色微变。
李纲顿时也面露怒色,道:“臣亦有所闻,自陛下登基以来,虽百官朝贺,却多有阳奉阴违之辈。近日更传出,有尚书私下与金使通书信,欲劝陛下议和!”
“议和?”赵恒冷笑。
“靖康之难才过去几个月,他们就忘了之前金人破城的时候?”
“朕若也信了他们那一套,临安怕是离沦陷也不远了。”
“这帮人,嘴上说抗金,骨子里想的不过是保身罢了。”
赵恒缓步踱回御阶,却没有坐下,只负手立于金龙盘柱之前,仿佛天地皆低。
赵恒忽然转身,沉声道:“宗大人。”
“臣在。”
赵恒沉默片刻,仿佛在压着什么情绪。他眼神沉沉地望着宗泽,忽然轻叹了一声。
“虽有你我之志,然朝堂之上——并非人人愿抗金。”
宗泽眉头一跳,眼神陡然一沉。
赵恒缓缓踱步,一边走,一边冷笑着摇头:“百官山呼万岁,忠心耿耿者口号不少,可真能披甲上阵、死战金寇的,又有几人?”
“这些人,早把祖宗江山当成他们的俸禄了。让他们写策论、议大政,他们头头是道,真叫他们送儿子上前线,个个推三阻四。”
宗泽一拳擂在胸口,声音带着几分愤懑:“陛下所言极是!臣宗泽,年过半百,尚可执戈!奈何那些戴乌纱的,不知家国为何物!”
李纲也上前一步,怒气冲冲道:“陛下,臣敢断言,若不早日清洗朝中那些奸佞,纵有万民从军,最终也会被这些人掣肘至死!”
赵恒没有立刻作答,目光缓缓移向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