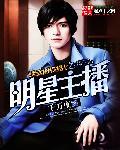趣书网>靖康耻?朕还在哪来的靖康耻?最新章节 > 第179章 拖出去斩了(第2页)
第179章 拖出去斩了(第2页)
他猛地一步上前,眼中杀气毫不掩饰:“你要是真不信我,那就别废话。现在就杀我,刀子快一点。”
“别整这些弯弯绕绕的把戏,没意思。”
说着,他往前一站,脖颈微扬:“来,把我头割了去,回头你可以写一封奏报说宋将诈降未遂,已伏诛,你这功劳也算是立得体面。”
屋内气氛陡然紧绷。
风从窗棂缝隙钻进来,灯影轻晃,撒里站在案后,手指摩挲着茶盏边沿,久久未语。
眼前这个人,明明身处敌营,孤身一人,命悬一线,却还能张口骂人、昂首等死,丝毫不显怯意。
这一刻,他忽然生出一丝狐疑:“这于海到底是真的胆大包天,还是这场戏,他们演得太像真的了?”
撒里的手指终于停了,盯着于海的目光里,最后一丝犹豫也被点燃殆尽。
他猛地一拍桌案,茶盏当地碎了半边,声音冷得像刀刮过金铁:“好!你嘴硬,你有骨头,那我就成全你!”
他转头喝道:“来人!”
门外顿时闯进两个亲兵,腰佩钢刀,面色森冷。
“把这姓于的拖下去,午门外当街砍了!”撒里眼中已无一丝笑意,冷声如霜,“头颅挂北城,尸体喂狼,给我金营上下提提神,看清什么叫诈降的下场!”
于海一愣,却随即哈哈大笑,笑得几近癫狂。
他朝撒里拱了个手,嘴角甚至带着一丝释然的血色讥诮:“好!干脆,够爽快!”
“我姓于的这一条命,本就捡来的。洮河那年冻水灌肺,是褚副帅背我三十里走出来的。你们若真信不着,杀了便杀。”
“只是——”他目光一凛,声音陡然低沉下去,“将来你若真领兵南下,打到韩营前头,别说我没提醒你有些门,是你们推不开的。”
“你今儿不信我,明儿可别后悔。”
撒里一言不发,只挥了挥手。
亲兵应声拖住于海,刀鞘磕地一声闷响,于海被压着往外走,脚步沉稳,一点不挣扎,只是肩膀绷得笔直,仿佛压得不是赴死的囚徒,而是踏阵的兵将。
院门外,夜雪纷飞,北风呼号如兽啸。
两名亲兵架着于海一路走至宅院偏门处,那是撒里府邸专设的处决空地,供临时处死军奴叛卒。
刽子手早已等候在侧,一把宽刃斩马刀横在石墩上,寒光森冷,血迹斑驳未干。
于海面无惧色,只扫了那刀一眼,便缓缓闭上了眼,口中低念一句:“褚副帅,若我回不去,就把我名刻在洮河边那块碑上。”
“死在金营,不辱军名。”
刽子手举刀在手,步步走近,喝令道:“跪下!”
于海一动不动。
亲兵正欲强按,忽然,远处一声炸雷般的喝声冲破雪夜,“刀下留人!”
那声音震得屋檐都颤了半下。
几人下意识停手,只见一道高大的身影风雪中奔来,披着狐裘,腰悬金符,正是行军司马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