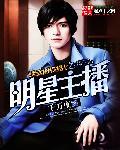趣书网>不顺心就要闹 第27章 > 第 145章 今天谢谢您的教导(第1页)
第 145章 今天谢谢您的教导(第1页)
第二天,王小小带着贺瑾去上学。
“姐,你怎么穿这么丑的衣服?”
“解剖室味道受不了,不要穿好的衣服,不然太臭了。”
王小小他们认为他们低调,但是两个小鬼一个穿得很好,一个穿得满是补丁。
两人骑着八嘎车,即使市里骑自行车比起县里的多,但是八嘎自行车还是很少的。
再加上他们利用二科,骑着八嘎车在军校里,即使两人不去主校区,但是还是引起注目。
第一天,她跟车来县城,时间控制不了,但是今天她自己来的,来太早了。
王小小推开解剖室的门,那股熟悉的、浓烈到令人窒息的福尔马林气味依旧扑面而来。
她是第一个到的。
空旷的实验室里,只有中央几张解剖台静静地矗立着,上面还残留着昨天课程留下的些许污渍和水渍,显得杂乱而潦草。
就在这一瞬间,眼前的景象与她脑海深处的记忆猛地重叠了。
不是严教员,而是她前世那位一丝不苟、吹毛求疵的博士生导师,那雷霆般的怒吼声仿佛穿越了时空,在她耳边炸响
“王小小!你的台面是菜市场吗?!”
“无菌观念!你的无菌观念被狗吃了吗?!”
“环境反映态度!一个连台面都收拾不干净的人,凭什么指望他在手术台上沉着冷静?!立刻!马上!给我恢复原样!”
几乎是肌肉记忆,她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
她快步走到水槽边,找到水桶、抹布和毛刷,又兑上一点能找到的消毒液。
先是用湿抹布彻底擦去所有可见的污渍,再用干抹布将台面上的每一滴水痕擦干,不留下任何湿漉漉的痕迹。
她对边边角角尤其苛刻,用刀子或刷子刮去那些极细微的残留。
毕竟她那个导师是个吹毛求疵的主,骂起人来,可以上至古今,下至爹娘祖宗。
这不仅仅是在打扫卫生,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对过去职业习惯的致敬,以此来安抚自己内心深处的秩序感。
当其他学员陆陆续续、叽叽喳喳地走进来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
昨天那个令人紧张和反胃的解剖台,此刻在晨光中泛着清洁而冷冽的光泽,一尘不染,井然有序。
而那个昨天在台上镇定得不像话的新生王小小,正背对着他们,一丝不苟地清洗着最后一把工具。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噤了声。
他们看着那光洁如新的台面,再看看王小小,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惊疑。
没人会想到提前来打扫解剖室,更没人会把它打扫到这种近乎变态的干净程度。
严教员夹着花名册走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一群学生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而那个最让他无语的女学生,刚刚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却极具冲击力的演示。
他的目光在光可鉴人的解剖台和王小小那张依旧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来回扫了一遍,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像昨天一样,冷硬地开口道“都愣着干什么?各自就位。今天,我们讲四肢的血管神经走向。”
但所有学员,包括严教员自己都知道,今天这堂课,在正式开始前,就已经被王小小用一块抹布,上了无比深刻的第一课。
上课,王小小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这时候的教学和她的教学不同,不能说对错,这个时代一个专业的医生才有多少,尤其导师更加少,医学成长换代有多快。
学习完后,王小小偷偷等着他们离开后,又去了解剖室,打扫干净,昨天不知道这里居然打扫敷衍,今天绝对不可以犯这个错误。
干净卫生,才能不会有任何病毒。
全部打扫干净,王小小对着解剖台已经离开的‘沉默的老师’鞠躬道谢。
“今天,谢谢您的教导。”
王小小背着包离开,赶到小瑾教学楼。
看见几人围在小瑾身边,贺瑾看到她,飞快的走了过来。
那几人看到王小小那身满是补丁的旧军装,又敏锐地嗅到了她身上那股福尔马林气味,脸上立刻露出嫌恶的表情,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互相交换着嘲讽的眼神,脚步也往后退了半步,仿佛她是什么不洁的东西。
其中一个领头的、穿着崭新蓝布学生装的高个子男生,撇了撇嘴,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人听见“哪来的乡下味儿?又是福尔马林又是土腥气,熏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