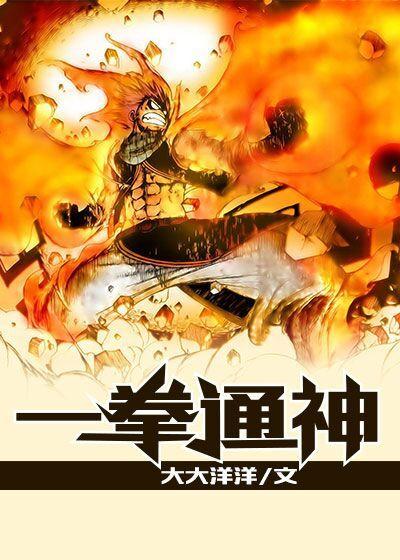趣书网>解白纱262免费阅读 > 第240章(第2页)
第240章(第2页)
桑盼怔怔抬起眼,反应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你是觉得,桑家人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定不会弃你于不顾,是吗?”
这个可能微乎其微,但如今孤立无援的境地,李淮颂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只能寄希望于此,他陡然回过神来,才发现这些年积攒的势力,不过成了左相手下的旗子,无论他也好,还是桑盼,真的有人把自己当作可以辅佐的人来对待吗?
“舅舅他……”
“他是个冷血的混账,至亲之人都疏离,又何况你我?”桑盼吸了口气,“他已将你看作废子了!”
双腿一软,李淮颂喉间梗住,半天没能说话。
“淮颂,今时今日的局面,你莫非甘心?”
那双眼又有些泛红了,李淮颂仰头看着她,心里想着。自始至终,他拼了命追赶着李淮仪的高度,却被无情甩在身后,心有不甘,终于见到机会,却又坠落至此,心中的疲累根本无法言说。
他无法理解桑盼的执着,至亲母子,明明他们离得这么近,他却总觉得看不清她。
“事到如今,娘娘还有什么法子?”
“我自然有办法,”桑盼盯着他,突然神经质地抽了抽嘴角,笑了一声,“棋还没下完,你不能走,他们都不能走!”
“我哪怕是死,也要见到胜负再死!”
*
大理寺承接起倒查旧案的事情,但处处受阻,查案进度很慢,接连几日过去,居然也仅仅是在层层权限之中,拿到了开旧卷宗的权力,官家同意倒查,却也态度模糊也许是还想顾念什么,但这点恻隐之心,却苦了下头办差的人。
想要阻挠倒查旧案的人不在少数,起码这几日来,陡然增多的额外事务,时不时出错的卷宗排布,真正呈上案头来无关的文书卷宗,都十分碍事,让原本就缓慢的进度几乎停滞。
杜含一个脑袋两个大,真正体验了一把这群老狐狸是怎么兵不血刃地给人添堵,自己一个官场新人,对上这群老畜牲,还是太显稚嫩。
至关重要的医案寻不到,那这桩糊涂账就要一直掰扯个没完,时日一久,官家不耐烦且是一回事,撑不撑得到有进展的那天又是另一回事了。
而另一边,代做铺子那边也传来邓翁的消息,早就静候多时的香娘子们由他带着,找到了平素里铺子夜间往汴河排污的口子,连同他们夜间偷天换日,以次充好的事情一时间全部被揭开,显露于百姓眼前。
原本御贡稳操胜券的宣和香局因此跌落泥潭,被无情地踹出行列,御贡的机会再次引起百家争抢。除却东京,上好的香铺子亦不少,栖风堂借此找回了口碑,重新加入了这场竞争中。
因此,林慕禾近来忙得脚不沾地,每日起得比顾云篱还早,与随枝一起忙碌于香坊的事情,到打烊后好一阵,才得以回来。
顾云篱手好得差不多时,买来木材弓弦,在铁匠铺打了许多箭簇,回了府后,便叮叮哐哐干起了木匠活。
接连三日,二人除了每日睡前的交流,几乎日日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
折腾数日,御贡的香样终于更精一步,连同一切需要的东西交予礼部,只等结果出来。
林慕禾也终于能喘口气,早早完工,回了府中。
院子里,一阵叮呤哐啷的声音引她的注意,洗过手,她穿过中庭,来到庭院中,看见了埋头鼓捣东西的顾云篱。
她穿着一身耐脏的青灰色外袍,头发随意束在脑后,几束不受控制散落出来,蹭在脸颊侧,都没能引起她的注意,只埋头干着手里的活计。
倒是听见林慕禾的脚步声后,她方才分神,仰头朝她看去,笑了笑:“今日的事情都忙完了?回来这么早。”
“忙完了,只等礼部后日张榜,若能得御贡机会,坊里还能开得更大了。”林慕禾说着,搬了个小凳子坐到顾云篱身边,看着她手里摆弄调试着一只已经成型了的弩箭。
原来这几日她每日在院中埋头苦干,是为了给自己做了个适手的弩。
“刚好,我也做好了。”顾云篱说着,掂了掂分量,“依着你手掌大小做得,你来看看?”
弩做得精巧,放在手里拿得正好,也可拿稳。
林慕禾笑了笑:“云篱连我手掌大小都知晓呢。”
后者不太自然地摸了摸鼻子,上手帮她熟悉弩箭:“你的手特别,我很早前,就记得清楚了。”
一支泛着银光的箭被放入卡槽,林慕禾分了神:“很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