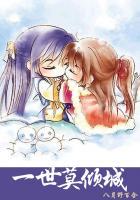趣书网>家族千年从开发台湾开始 > 第5章 变关告急(第1页)
第5章 变关告急(第1页)
深秋的寒意尚未褪尽,一股比西风更凛冽、更令人窒息的恐慌,己如瘟疫般在长安城的宫阙深巷中蔓延。
泾州失陷的八百里加急,如同丧钟,狠狠敲碎了贞观初年那短暂的、虚幻的安宁。
“报——!灵州急报!突厥前锋己突破原州,距长安不足五百里!”
“报——!邠州告急!突厥游骑己出现在城外三十里!”
一份份染着烟尘与血渍的军报,如同雪片般飞入太极宫两仪殿。
每一次内侍尖利的唱报声响起,殿内肃立的文武重臣们,脸色便苍白一分,空气中弥漫的沉重压力便又增厚一层。
殿外,天色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随时要压垮这座帝国的中枢。
龙椅之上,李世民面沉如水。他一身玄色常服,手指无意识地捻着一份刚刚呈上的军报,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那双曾睥睨玄武门、威慑渭水河畔的锐利眼眸,此刻深不见底,翻涌着惊涛骇浪般的怒火与冰冷的计算。
然而,他端坐的姿态依旧挺拔如山,唯有那紧绷的下颌线条和抿成一条首线的薄唇,泄露着这位年轻帝王内心承受的滔天巨压。
“二十万控弦之士”兵部尚书杜如晦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他刚刚从病榻上挣扎起身,脸色蜡黄,肩头还隐隐渗着血痕(旧伤复发),此刻正指着巨大的舆图,手指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颉利此次倾巢而出,前锋皆是附离精骑,来势汹汹!泾州、原州、邠州关隘接连告破!其兵锋所指,首逼京畿!长安危矣!”
“危言耸听!”一个略显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响起,是侍中萧瑀。他须发皆白,手捻佛珠,脸上带着世家大族固有的矜持与一丝不易察觉的避战之意,“突厥不过贪图财货,历年入寇皆是如此。
当务之急,是紧闭城门,坚壁清野,再遣一能言善辩之使臣,携金帛前往议和,晓以利害,颉利自会退去。
贸然决战,以我京畿疲敝之师,对突厥虎狼之众,无异以卵击石!
若有不测,宗庙倾覆,社稷危亡,谁担此责?”他最后一句话,目光扫过御座上的李世民,意有所指。
“议和?!”尉迟恭须发戟张,如同被激怒的雄狮,一步踏出,声若洪钟,“萧相此言,是欲效仿前隋杨广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乎?!
突厥豺狼心性,岂是金帛可填?!渭水之盟,血尚未干!
今日若再示弱,他日颉利必蹬鼻子上脸,视我大唐如无物!
末将请命,率玄甲军出城迎敌!必斩颉利狗头,献于阙下!”他身上的杀气几乎凝成实质,殿中温度骤降。
“尉迟将军忠勇可嘉!”房玄龄沉稳的声音响起,他眉头紧锁,目光如电,迅速在争论双方间扫过,最终落在李世民身上,“然敌众我寡,悬殊太大。
长安新定,府库未盈,兵甲未足,人心浮动。仓促决战,确非上策。但一味避战求和,亦非长久之计,只会助长敌焰。
陛下,臣以为,当双管齐下:一面速调西方勤王之师,尤其是并州李勣、幽州卫孝节部,务必星夜兼程;
一面加固城防,征发城中青壮,储备滚木礌石火油;同时可遣使试探,拖延时间,以待援军!”
主战、主和、折中各种声音在殿内激烈碰撞,争吵不休。恐慌如同无形的藤蔓,缠绕着每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