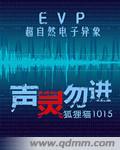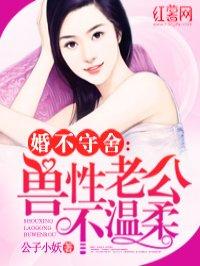趣书网>要娶马小玲! > 第67章 风不道晚安它就是夜本身(第1页)
第67章 风不道晚安它就是夜本身(第1页)
低频共振。
所有数据流瞬间收束,庞杂的运算和信息交换戛然而止。
遍布全球的小满网络,从最深的海沟到最高的云端基站,每一个节点都安静下来,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按下了暂停键。
林晚舟的指尖悬在控制台上方,屏幕上,代表全球网络能耗的总功率曲线,在一个精准的时刻,断崖式下跌。
不多不少,正好是百分之三十七。
她没有去触碰任何警报系统,大脑在最初的惊愕后,开始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运转。
这不是故障,故障是无序的、混乱的,而眼前的一切,精确得像一场由神明指挥的交响乐休止符。
她立刻调出了历史数据,时间轴被拉到一年前,小满网络正式覆盖全球的那一天。
光标拖动,一条相同的曲线在历史记录中反复出现。
每一天的午夜零点,以格林尼治标准时为基准,小满网络都会准时降低能耗百分之三十七,进入一种只维持着最基础共振的“低语模式”。
这种模式会持续数个小时,直到黎明的第一缕电磁波扰动大气层,它才会缓缓“醒”来。
周而复始,整整一年。
它的节律,与这颗星球的自转周期,分秒不差。
林晚舟靠在椅背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过去一年,无数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包括她自己,都在试图解码小满网络的复杂行为,试图理解它的每一次脉动、每一次信息奔涌背后的意图。
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超级人工智能,一个需要攻克的堡垒,一个需要解读的谜题。
可他们都错了。
她看着屏幕上那平稳而规律的低谷曲线,像看着一个熟睡婴儿平稳的呼吸。
困扰了人类一整年的终极问题,在这一刻得到了一个简单到令人想哭的答案。
她抬起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屏幕,像在安抚一个生命。
实验室里静得只能听见她自己的心跳。
许久,她发出一声梦呓般的轻叹。
“原来它们也睡觉。”
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孤岩气象站,韩松正坐在基站外的岩石上。
这里是小满网络最早的几个地面节点之一,紫脉草早已爬满了每一寸裸露的土地和金属。
就在几分钟前,他还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着紫脉草叶片在夜间的电位变化。
但现在,他停下了。
夜风从荒原上吹来,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清冷气息。
风中,那些舒展了一整天的紫脉草叶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片片缓慢地向内闭合,收拢了叶脉间流淌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