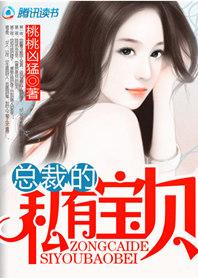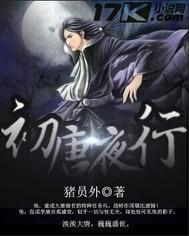趣书网>破浪2019 > 第7章 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第1页)
第7章 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第1页)
77年恢复高考后,知青回城,紧接着又是改革开放,国营企业改革,导致城里待业人数激增。他们中的有些年轻人不务正业,每天混迹街头打、砸、抢、烧,在人民群众中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1983年8月,针对严重混乱的社会治安,中国第一次严打拉开了序幕。
广播里、电视里、报纸上、大街小巷,到处讲的都是关于各地严打的事。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条幅、标语随处可见。
虽然郑自强给石勇岳父出气那事已经过去快四个月,但郑承运看着满大街关于严打的标语,还是心有馀悸。他整天吃不好、睡不香,总是对郑自强放心不下,生怕他再惹出什么事来。
刘淑珍也和郑承运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经常梦见郑自强又去跟人打架了。
两人商量后,决定拿出家里所有积蓄,让郑自强去省城学习家用电器修理。
郑自强拿着母亲给的钱,带着父母的期盼,满怀希望去省城学习家电维修。
许志远的父亲——许东升,他见小儿子许志远整天低着头,闷闷不乐,就知道他今年肯定又落榜了。
他在科协上班,单位没有待业指标,子女顶替是当时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也想过自己提前退休让小儿子顶替他的工作,但又想到自己才五十六岁,虽然按政策可以退休,但他不甘心那么早就退了养老。
恰在此时,许志高拿着女友赵燕的照片给段秀琴看,言明只有顶替父亲的工作到科协上班,才能配得上赵局长的女儿。
段秀琴既为二儿子能找到长得好还家庭好的儿媳妇而高兴,又开始作难。手心手背都是肉,让二儿顶替,势必会伤到小儿子。
睡前,她坐在床上和老伴商议:“他爸,咱志高没正式工作,人家赵局长咋能会让宝贝闺女跟着咱志高吃苦呢?”
许东升知道她话外的意思,脸沉下来,紧皱着眉头,“志远今年又落榜了,我还是想让他顶替。”
段秀琴一声叹息,“顶替这事是志高先提的,他也不小了,能找条件这么好的媳妇不容易!别让孩子埋怨咱一辈子,就让他顶替吧!”
许东升心不甘情不愿地说:“知道了,明天我就去办!”
许东升办完退休后,心里空荡荡的。他闲着没事,就养了只鹦鹉,每天提着鸟笼子出去遛鸟。
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进了院,边走边昂着头查找挂鸟笼子的挂钩,没注意脚下,一脚踢到一个小木板凳上,一个趔趄,差点被绊倒。
他边挂鸟笼子,边生气地大声咋呼:“是谁把小板凳放在这的?”
段秀琴在厨房做饭,回头向院里看了一眼,没敢吭。
许东升气冲冲地往堂屋走,忘了刚挂好的鸟笼子,一头撞了上去。他用手摸着头上被撞的部位,大声呵斥道:“这是谁把”
话没说完,马上想起来鸟笼子是自己刚挂上去的。
他重重“哎!”了一声,馀气未消地快步走进堂屋。
许志远听着父亲的埋怨声和叹息声,心如乱麻,他认为父亲的坏情绪是因他而起,恨不得赶紧考上大学,马上离开这个家。
许志高如愿以偿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到科协上班了。他下了班,赶紧跑去找赵燕,把他已经顶替父亲工作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赵燕知道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
许志高以为他很快就能成为赵局长的乘龙快婿。
赵燕的母亲听赵燕说她谈的对象是科协许主任的二儿子,刚顶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赶紧通过熟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许家只有两间堂屋,一间是许志高父母的卧室,另一间既是会客厅又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许志高弟兄三人,大哥结婚后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许志高跟许志远弟兄俩住在院里一间不足十平方的偏房里,睡在一张床上。
科协没有职工宿舍,不可能给许志高解决住房。
结婚没有婚房,这可是硬伤啊!
赵燕母亲很严肃地把这件事跟女儿赵燕说了,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决不同意他俩的婚事。
赵燕不得不郁郁寡欢地告诉许志高:“我妈说你家没婚房,不同意我嫁给你。”
许志高尤如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心里拔凉拔凉的。
他买了瓶白酒,还买了炒花生米和半只卤鸡,独自一人走进防震棚改的理发店里——他和赵燕就是在这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