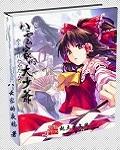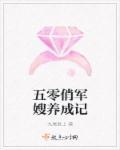趣书网>男主秦思齐 > 第105章 归乡(第2页)
第105章 归乡(第2页)
“祭祖宗!应该的!”
“晚上都去祠堂!”
人群爆发出赞同的呼声。在村长和几个族老的劝说下,村民们这才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地慢慢散去,议论声和笑声依旧在热风中飘荡。
在村长家草草吃过一顿便饭,新鲜的时蔬,金黄的炒鸡蛋,还有一小碟腊肉。
吃完饭,秦思齐说道:“娘,您在村长家再歇息一会儿,消消暑。家里久未住人,等会我们再一起收拾家。”
秦思齐没有休息,走到了前院,曾经的私塾,回到了启蒙和苦读的房间。
推开木门,房间和课桌上没有灰尘,看来是有人经常来扫过卫生。但房间里早已空无一人,几张桌椅依旧摆着,有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他一步步走过去,在曾经的位置坐下。
腰背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如同当年那个如抓到救命稻草的孩子一样,发奋读书,总想着给恩师留下最好的印象。
就在这片寂静中,一个熟悉而威严的身影,仿佛从时光深处缓缓走来,清晰地出现在讲台的位置,那是他的恩师,夫子依旧是青布长衫,手里还捏着一卷书。
秦思齐的心猛地一紧,一股酸楚和思念瞬间涌上鼻尖。仿佛又听到了老夫子抑扬顿挫的吟诵声,感受到了那严厉目光下深藏的慈爱与期许。
讲台上的“恩师”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极其少有的欣慰笑容。他赞许地点着头,目光中充满了肯定与骄傲。
秦思齐眼眶瞬间湿润了。他张了张嘴,想对恩师诉说这一路的艰辛,想倾诉考中时的狂喜,更想表达心中无尽的感激。他想说:“先生,学生回来了,没有辜负您的教诲”
“思齐哥!思齐哥!原来你在这儿啊!”一个焦急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打破了这凝滞寂静。
秦思齐浑身一颤,猛地回过神来。讲台上空空如也,哪有什么恩师的身影?只有太阳投射见来的光影。方才的一切,不过是思念和情感激荡下产生的幻影。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失落与怅惘,转头看去。村长的儿子秦明慧正站在门口,额头上还挂着汗珠。
“明慧哥,怎么了?”
“可找到你了!”秦明慧喘了口气,“我爹(秦茂山)让我来寻你,说趁着日头还没有彻底落山,让你赶紧去各家各户拜谢!东西都已分好了,明文哥他们正等着你。”
秦思齐站起身,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张空荡荡的讲台和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座位。
就在他转身欲走的瞬间,眼角的余光仿佛又瞥见,那空无一人的讲台旁,青衫的衣角一闪,恩师那带着欣慰和鼓励的笑容再次浮现,随即如同水汽般消散在空气中。他仿佛听到一声无声的叮嘱:“去吧,孩子。”
“好,我这就去。”秦思齐定了定神,对秦明慧点点头,大步走出了这承载了他太多记忆的村塾。
秦茂山早已指挥着秦明文、秦明武和其他几个本家年轻人,将带回来的布匹、日用品按户分好,堆成了小山。秦思齐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青色细布长衫,秦思文等人则挑着一副担子,里面装满了分好的礼物。
按照村里的排序,每一家,秦思齐都亲自登门。
第一家,秦三公家。第二家,大伯秦大安家。第三家,秦茂山家每家一匹布,加上一些日用品。
一家接着一家,一户连着一户。无论家境贫富,无论当年资助是多是少,秦思齐都执晚辈礼,恭敬作揖,真诚道谢。
他的声音渐渐有些沙哑,背脊却始终挺得笔直。每一户人家,接过那代表着秀才公心意的礼物时,脸上都绽放出由衷的笑容和自豪。那些朴实的夸赞不绝于耳:
“思齐真是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瞧瞧这气度,不愧是秀才老爷!”
“老秀才教得好啊!秦家嫂子有福气!”
而几乎在秦思齐离开每一家时,都能听到身后传来类似的吩咐:
“孩他娘,别愣着了!赶紧去思齐家,看看有啥能帮忙打扫收拾的!秀才公家可不能乱糟糟的!”
“去菜园子摘点新鲜的瓜菜,给思齐家送去!”
“把咱家那只老母鸡捉上,晚上给秀才公炖汤补补!”
“二小子,去劈点柴火,送到思齐家灶房去!”
男人们则大多留在自家门口,目送秦思齐远去,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互相议论几句,然后不约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秦氏祠堂走去。他们要去帮忙打扫、布置,准备晚上秀才公的讲话。
祠堂里的灯火,即将为这个炎热的夏夜,点燃最庄重也最温暖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