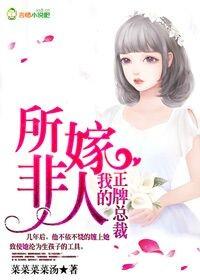趣书网>男主秦思齐 > 第119章 重视功名(第1页)
第119章 重视功名(第1页)
交完税后,白湖村的车队飞快驶离这片是非之地。车轮碾过黄土路,快速离…
车上,除了带回那张盖着鲜红官印、注明“完税”的回执,还有几十袋未曾动用的“余粮”,那是因评了“上等”而比预期少缴的部分。
沿途,其他村庄还在烈日下苦苦排队的农户,目光羡慕看着白湖村的车队。那眼神里充满了嫉妒,最终都化作一声声沉沉的叹息。
有人低声议论:“瞧见没?那是白湖村的!人家村里出了个秀才,有读书人就是不一样,连粮吏都得给几分脸面……”“那几十袋余粮,省下来就是几家人的嚼谷啊!”
秦茂山坐在头一辆牛车上,腰杆挺得比来时直了许多。摸了摸怀里那张硬挺的税票回执。
秦大安等人推着车,脚步也轻快了,低声交谈着,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庆幸笑容。偶尔有风吹过,带来后方官仓前隐约的呵斥和踹斗的“嘭嘭”闷响,他们的笑容会僵一下,随即又加快脚步,仿佛要将那令人心悸的声音彻底甩在身后。
到了官道岔口,秦书恒和秦文阁停下脚步。两人穿着县衙户房的青色吏服,在夕阳余晖下显得格外体面。
“茂山叔,思齐,就送到这儿了。”秦书恒拱手,姿态恭敬,脸上带着亲热,“族里缴粮顺遂,我们两已经在衙门安稳了跟脚,日后族中但有事,尽管差人到县衙寻我们便是。”
辞别了秦书恒二人,车队继续前行。远离了官仓的压抑,气氛彻底活络起来。汉子们开始高声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谈论着省下的粮食能多打几斤肉、扯几尺布,谈论着家中等着他们的婆娘娃娃。
笑声在乡间土路上回荡。秦思齐听着这充满烟火气的喧闹,感受着族人们发自内心的轻松与喜悦。
车队还未进村,消息就像长了翅膀,男女老少,几乎倾巢而出,脸上洋溢着比过年还兴奋的笑容。
“回来了!回来了!”
“村长!大安!顺当吗?”
“余粮!真有余粮带回来了!”
欢呼声、询问声瞬间将车队淹没。妇人们涌上来,七手八脚地帮着卸车,摸着那沉甸甸的粮袋,脸上笑开了花。孩子们在人群中兴奋地钻来钻去,小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粮袋,仿佛看到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过年才能尝到的肉味。
秦茂山被众人簇拥着,站在碾谷子的石磙上,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带着扬眉吐气的激动:“托祖宗保佑!托思齐的福!咱们白湖村的粮,验的是上等!缴得顺顺当当!一粒‘耗损’没多扣!还余下这十几袋!”他指了指那几袋格外显眼的“余粮”,人群里立刻爆发出更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看看!看看!”人群里,七叔公激动地用拐杖杵着地,花白的胡子一翘一翘,“当初,族里咬牙供思齐读书,多少人背后嚼舌根子?说供个读书郎不如多买头牛!说砸锅卖铁是瞎折腾!如今呢?啊?这一趟省下的粮,值不值?值不值?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老人家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值!太值了!”人群爆发出震天的回应。
“思齐是咱村的文曲星!是咱村的福气!”
“往后谁再敢说读书没用,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
“就是!思齐在,县衙里都有人照应!这叫什么?这叫朝中有人好办事!”
赞誉如同潮水般涌向秦思齐。无数道热切、感激、甚至带着点敬畏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那些曾因免税田分配、因书童银钱而私下嘀咕过、眼红过的人,此刻脸上只剩下了由衷的庆幸和与有荣焉的自豪。
选择供秦思齐读书,成了白湖村最英明、最值得夸耀的集体决策。秦思齐,这个年轻的秀才,在村民们朴素的心中,已不仅仅是一个有功名的读书人,更成了凝聚族运、带来实实在在庇佑的象征,是“文气”的代表!
秦思齐站在人群中,承受着这汹涌的赞誉,脸上维持着谦和的微笑,心头却五味杂陈。他清楚,这份“庇佑”沾着取余村的血泪,是建立在特权与不公的脆弱冰面上。乡亲们越是感激,他肩上的担子便越是沉重。
自那日起,秦思齐家那小小的灶房,彻底成了村里感恩戴德的“圣地”。妇人们表达心意的热情,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汹涌浪潮。
清晨,天刚蒙蒙亮,院门就被轻轻叩响。刘氏披衣开门,门口台阶上,往往已悄然放着一小捆带着露水的嫩青菜,或是一小篮鸡蛋。有时干脆是一碗刚出锅、冒着热气的肉,油汪汪的,香气扑鼻。
“思齐娘,趁热给秀才公端去!读书费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