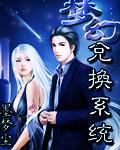趣书网>明末崛起打造一个崭新华夏帝国 第八海 > 第1078章 摆烂的崇祯(第1页)
第1078章 摆烂的崇祯(第1页)
周延儒鼻尖一酸,慌忙依礼制跪下,声音竟有些哽咽:“臣……周延儒,叩见陛下”。
崇祯正伏案看着一份文书,闻声缓缓抬起头。
他的动作有些迟缓,目光在周延儒身上停留片刻,似乎才聚焦看清来人,“周先生平身吧”,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倦意。
一旁的老太监王承恩,也是面色灰暗,悄无声息地搬来一个绣墩。
周延儒谢恩,却未立刻起身,而是郑重地行完大礼,方才起身略欠着身子坐下。
君臣二人相对,一时竟相顾无言。
偏殿内寂静得可怕,只有炭盆中偶尔爆出的一声轻微“噼啪”响,以及窗外呜咽不止的风声。
那风声,像极了大明帝国日渐微弱的呼吸。
崇祯将手中的文书随意丢在案上,出“啪”的一声轻响,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周先生此时进宫有何要事?”。
他的目光没有看周延儒,而是投向窗外那灰蒙蒙的天空,眼神空洞。
周延儒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翻腾。
他知道,皇帝虽看似憔悴欲倒,但那多疑敏感的性子却从未改变,甚至可能因巨大的压力而变本加厉,他必须字斟句酌。
周延儒深吸一口寒气,终于不再迂回,将京城的惨状血淋淋地撕开在皇帝面前。
他声音沉痛,描述了外城易子而食的地狱景象,内城百姓掘食草根的绝望,以及那弥漫全城、无法驱散的死寂与骚动并存的恐怖气息。
他重重叩,声音带着绝境下的嘶哑:“陛下!京城粮尽,秩序将崩,臣已智穷力竭,伏乞陛下圣断!”。
一阵漫长的沉默,殿内只剩下炭火噼啪作响,仿佛在灼烧着这令人窒息的寂静。
终于,崇祯缓缓地、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开口,声音幽冷得如同殿外的寒风:“周卿,你乃内阁辅,揆席百僚。治理国家,绥靖地方,不正是你的份内之责么?”。
他缓缓站起身,那空荡的龙袍更显其身形的瘦削,踱到窗边背对着周延儒,望着窗外死灰色的宫墙,声音里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近乎自嘲的平静。
“以往,很多人,很多奏章,都说朕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对臣工缺乏信任,动辄苛责诘难”。
说到这里顿了顿,仿佛在咀嚼这些评语,“朕……深以为然,也欲改之”。
他猛地转过身,那双深陷的眼睛里骤然爆出一种混合着痛苦、怨愤和极端压抑的疯狂光芒,死死钉在周延儒身上。
“所以!朕吸取了教训!朕不再事事过问,朕将国事尽数委于尔等内阁,委于你这辅!朕只求不再担那‘独夫’之名!可如今呢?”。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变得尖锐刺耳,“如今局面糜烂至此,你拿不出方略,却又来问朕?来给朕说这些?!朕还能有什么办法?啊?!你说!朕还能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