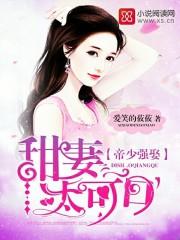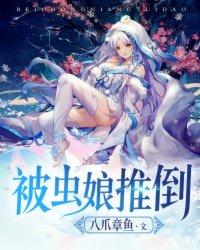趣书网>苏德战争 1941年 战役 > 第173章(第1页)
第173章(第1页)
在大战年月里,丘吉尔对斯大林、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决非始终一贯而是变化很大的。战争初期,他根据简单的逻辑认为希特勒的敌人就是英国的朋友,丢掉了一切关于与共产主义结盟是否明智的顾虑。他与苏联的交往以及当时的观点似乎都带有乐观主义和同志式信赖的色彩。1943年8月,丘吉尔对哈里曼说,展望前景,将有腥风血雨。他认为斯大林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跟他打交道会有严重的麻烦。然而在这种阴郁的现实主义病症的发作中,丘吉尔似乎过分夸张地强调了在与斯大林打交道的他个人品格所起的作用。甚至直到1944年秋,丘吉尔还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过,与斯大林会谈时气氛如何诚挚,他甚至进一步说到,他相信斯大林并不是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人,说他相信这个独裁者容易受到党和军方极端分子的巨大压力。这一看法,本身就说明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思想和他的政府的性质缺乏认识。可是1945年初,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丘吉尔给在旧金山的艾登的一封电报中注意到了俄国向易北河推进时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竭力敦促美国人在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时应采取强硬的态度,除非能就解决波兰问题,以及苏联在巴尔干和中欧的占领政策中从莫斯科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这种真知灼见已迟了四年,在美国根本无人理会。
苏联政府以一张人身安全保证书为诱饵,将隐藏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骗出来,只是为了把他们逮捕起来,并判处长期监禁。1945年5月,杜鲁门总统派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想解决棘手的波兰问题,争取释放被捕的波兰人。两个目的他一个都没有达到。7月5日,英国应杜鲁门的要求宣布承认新的波兰临时政府,这实际上是前卢布林共产党人傀儡政权,过后不久,英国撤销对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新波兰和它的政府完全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了。
波兰是这样,中欧和东欧的其它地方也是这样。贝奈斯,一个乐观主义的亲俄分子,不顾艾登的忠告,于1943年12月赴莫斯科去签订苏捷条约。他的内阁的五分之一的职位要让给经莫斯科训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贝奈斯就这样让这种有朝一日要毁掉马萨里克和自由捷克斯洛伐克的分子进入内阁。可是,当时贝奈斯还告诉在莫斯科的哈里曼说,他十分满意,苏联的意图可以信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再向他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决不会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
1944年8月对罗马尼亚的侵占蹂躏,已经描述过了。当年4月,莫洛托夫在广播中还保证说,苏联无意干涉罗马尼亚内政,可是在根据罗马尼亚国王的命令,逮捕了安东奈斯库以后,共产党人开始策划和煽动反对温和而又无能的萨纳捷斯库政府。这种煽动是由莫斯科通过安娜&iddot;波克尔和共产党人的全国民主阵线一手导演的。萨纳捷斯库政府让位于勒德斯库领导的联合政府,但是莫斯科也无意让这个政府生存下去。罗马尼亚因赔款而被弄得贫困不堪,驻布加勒斯特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苏方主席维诺格拉多夫,事先未与英、美同僚商量就对罗马尼亚政府发号施令。3月6日,维辛斯基访问布加勒斯特并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解放了勒德斯库政府,由格罗查为首的政府来取代它,这是一个华盛顿和伦敦拒不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
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局的演变也大同小异。美英代表是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根本没有实权,没有人向他们反映情况,也没有人找他们磋商问题。南斯拉夫由于莫斯科训练的铁托的游击队的参加而幸免于苏联占领,据信铁托是坚定地站在苏联阵营一方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苏军占领时故意把西方的代表排斥在外。只有在希腊,人民的自由才没有被剥夺,而这完全是因为有英国军队存在的缘故。
美国总统的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同意约瑟夫&iddot;戴维斯对丘吉尔的评价,当时他把丘吉尔描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不过首先是一个伟大的英国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而不是维护和平。霍普金斯也是从英俄争夺权力的角度来向杜鲁门解释丘吉尔的行动的。历史将对这两种判断都提出疑问。没人可以怀疑丘吉尔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首先表现在及早认清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他以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指挥了英国的抗战。然而1940年他接过政府权力的时候,他的国家仍是资源十分丰富、独立自主的,可是到1945年,他却使它变得贫穷困顿,不得不受美国的保护了。英国在船只和收入方面的损失十分惨重,到1945年,英联邦,特别是联合王国,在经济上已经十分依赖美国的援助和贸易了。然而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和欧洲强国的突然衰落不能仅仅用财富和资源的损失来解释,因为1945年英国在军事上和潜力上仍十分强大,英国在经济上的损失与苏联相比,也只不过是个零头。苏联在战争年代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物资援助。
苏德战争一爆发,丘吉尔和他的联合政府即同苏联结成联盟,在当时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其它的选择余地。可是丘吉尔有一个简单化了的目的,即打败希特勒德国。他不允许其它的因素来干扰他的谋略。由于这一压倒一切的使命,加以害怕苏联退出战争,丘吉尔对斯大林加给他的中伤和侮辱,几乎是不加斥责地接受了下来。后来他发现别人用近乎讹诈的策略来逼迫自己。他同斯大林不同,没能在这场斗争的最初日子里就设想战后结果,以便力争不仅赢得战争还要赢得战后的和平。据说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分子丘吉尔竭力抑制自己的种种疑虑,为了更好地进行这场战争而强使自己与苏联合作。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他的著作表明,至少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对共产主义的性质、苏联的愿望和手段了解不多,在与莫斯科的交往中,甚至迟至1944年,他有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和信任,而以往的经验和事件证明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