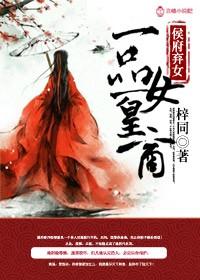趣书网>大雪龙骑系统 > 第59章 坐骑(第2页)
第59章 坐骑(第2页)
不多时,一位身着青色长袍官服、气质儒雅干练的中年男子步入书房,正是安南伯府长史李昭。
“伯爷,您唤我?”李昭恭敬行礼。
“昭兄,”秦昊抬眼看向这位得力臂膀,开门见山地问道,“今年州府之中,可有什么实干良才?”
“良才么”
李昭略作沉吟,脑中飞快闪过几个人选,随即答道,“州府衙署内倒有一名年轻小吏,名唤张谦。”
“此人虽职位不高,然心思缜密,处事练达,尤擅庶务,颇有实干之才。”
“依下官看,或可符合伯爷所求之‘良才’。”
“善!”
秦昊当即拍板,“便是此人了,另外,你再于各衙署中,挑选几名能独当一面的官吏,与他一同准备。”
“不日之后,前往北凉州阳谷县听命!”
李昭心中略感意外,但还是迅速拱手应道:“下官遵命,即刻去办。”
“管家!”
秦昊又转向侍立一旁的管家,“持我军令,速去明良城大营。”
“传令李将军,从虎贲营中抽调两百精锐骑兵,其中必须要包括一名炼脏境的千夫长。”
“命他们护送这批官员前往北凉州阳谷县,待官员安全抵达后,这支兵马亦不必折返,就地留驻阳谷县,听候县牧秦良调遣!”
“是,伯爷,老奴这就去办!”
管家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领命而去。
书房内重归寂静。
秦昊缓缓起身,负手踱至窗前,目光穿透庭院,遥遥望向北方那片苍茫之地。
“良儿,为父眼下能为你做的也唯有这些了。”
“前路漫漫,望你珍重。”
此刻,身处阳谷县衙后院的秦良,自然无从知晓父亲在千里之外为他所做的安排。
他正沉浸于短暂的休憩时光。
翌日清晨,天光微熹。
秦良便已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县衙大堂之上,开始了新一日的公务。
得益于前期雷厉风行的政令与民众的辛勤劳作,阳谷县境内大片荒芜的土地已被开垦出来,绿油油的麦苗覆盖了昔日的荒野,生机盎然。
然而,秦良的思绪并未止步于此。
他深知,粮食丰产仅是夯实根基的第一步。
若想真正让阳谷县富庶强盛起来,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就必须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其他产业。
阳谷县最大的地利,便是紧邻那条奔腾不息的阳谷河!
发展渔业,无疑是条康庄大道。
但秦良也知道,发展渔业的前提,是必须先降服这条喜怒无常的大河!
阳谷河作为北凉州北部的水系命脉,贯穿诸多支流,丰水期极易泛滥成灾。
若不根治水患,贸然鼓励民众下河、百姓挖塘养鱼,无异于沙上筑塔,一场洪水便能将所有心血化为乌有。
经过反复权衡,秦良初步定下了治水方略。
当务之急,是修筑坚固的河堤与四通八达的引水、排涝水渠。
至于建造大型水库这等浩大工程,虽效益长远,然所需人力物力堪称海量,绝非当下这战事频仍的北凉州所能承受。
在乱世边陲,务实的选择是先求稳固,再图发展。
计划既定,秦良立刻付诸行动。
他一面动员百姓们利用阳谷河的便利水源,在规划好的安全区域挖掘鱼塘,为渔业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