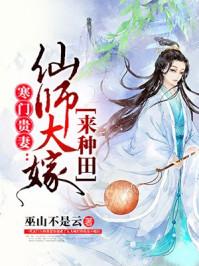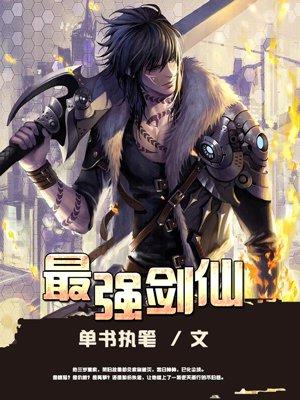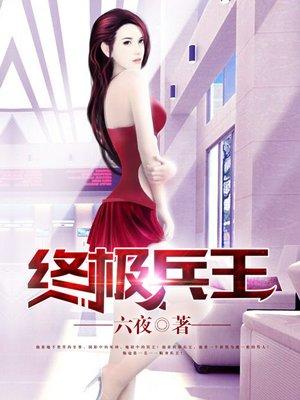趣书网>隆庆中兴TXT免费 > 第1907章 干戈指处狂寇消六(第1页)
第1907章 干戈指处狂寇消六(第1页)
对于朱载坖的这个想法,重臣也是很无奈,摊上朱载坖这么一个皇帝,对于臣子们来说确实有些无奈的,除了成祖之外,大明最好战的皇帝非朱载坖莫属,幸好武宗这个庙号已经被定了,否则朱载坖也绝对是武宗庙号的有力竞争者,而且朱载坖对于什么无为而治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朱载坖一向是主张积极治理的,当朱载坖的阁臣是极为痛苦的。
当然除了内阁之外,朱载坖还命令兵部、户部、刑部和两广总督上疏讨论彻底安定两广徭乱的办法,内阁与相关的部院详细整理了有关大明对于两广地区的治理过程,在大明初年,官府不直接与瑶人产生联系,而是中间人抚瑶官与瑶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类似于土司的羁縻统治。
在这种统治之下,广西在大明初年确实是相对比较安定的,朝廷尚未实现深入统治的广东瑶区,以量授与官的羁縻形式与地方大族合作,官府官员和地方州民可以凭借自身或家族所在地区实力招抚瑶人归顺,从而获得政治上的上升通道。瑶人被封为瑶负责管理下属瑶人事务不仅代表着个人政治地位的获得,更是对其所在山林权利的承认,其下属瑶人也获得了朝廷的身份认同,不再被打上“瑶贼”或“盗”“寇”的身份标签,并被赐予敕免赋役的经济特权,纳入到大明朝廷统治之内。
同时这个时候的大明兵强马壮,对于这些瑶人来说还是有很强的震慑力,因为成祖时对于安南的征讨使得这些瑶人看到了大明的强大,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还是能够和瑶人和平共处,瑶人也比较恭顺,在这一时期岭西的瑶人在瑶的带领下入京进贡表示归顺,或在抚瑶官员的招抚下纳入版籍。
但是随着朝廷放弃安南,大明初年的这种管理瑶人的策略弊端就日益明显了,其招抚太滥,后世不可守成。先这一政策未能实现对瑶人的基层控制,抚瑶官员在承袭上往往失去了对瑶人掌控,其作为互惠互利的朝贡贸易也在后期成为地方官员压榨剥削瑶人的工具,激起了瑶人的反抗,而且朝廷试图控四夷而制天下,但在具体措施上其抚瑶政策的实质仍是羁縻远人,未能真正地将瑶人纳入到大明朝廷统治中,成为大明编户齐民的一部分。地方官员招抚失策,大明武备空虚都是激起瑶人反抗的重要原因。
而自正统以来,北方边患愈演愈烈,朝廷的主要精力都在对付蒙古人上面,所以对于广西所能够投入的精力就极为有限了,对于瑶乱往往小乱不管,大乱出兵征剿,是为必不得以而用兵。虽然朝廷也曾经大举出征征讨瑶人,但是也只能管一时,不能起到长治久安。
殷正茂在奏疏中就认为,朝廷之前姑息招抚,而无震慑之威,所以导致地方上瑶乱愈演愈烈。成化以来,以来在两广总督的主持下对岭西作乱瑶人多次动征剿。但并未能起到良好效果,其主要在于征剿不彻底,未能彻底平定动乱,或是平乱之后未能妥善完成善后事务。如在嘉靖年间,张经本来已经将徭乱安定下来,准备实施后续政策,但是倭乱复起,朝廷不得已将张经调走,这些事情都使得徭乱不能够被彻底平定下来。
兵部尚书徐渭也认为,瑶乱纷纷,东平而西叛,南靖而北攘,如吹羹止沸。招抚太滥不可守成。而自正统年间开始,剿之不能彻底平定动乱,抚之则不得其法,地方往往姑息瑶人,使得徭乱永不能终结,这是一个极为麻烦的事情。
兵部认为先还是要大举征讨,先以征讨安定广西,然后再重建秩序,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处理岭西瑶乱,并采取多种善后事宜实现对广西地区的有效控制。兵部和殷正茂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徐渭和殷正茂都认为必须要以严酷手段对于这些瑶民予以镇压,实施改土归流,加强朝廷对于此地的控制,然后广设州县,开辟粤西驿道、西山大路并疏浚水路,由此不断加强广西地区与外界的联系。
瑶人所恃者,不过是高山险阻、万山遍布,是王化所不能及之地,所以当地瑶人往往恃险为乱,地方官府亦无法实现深入控制。所以要先征剿,现在修路,使得朝廷对于这些地方控制得以加强。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由瑶至民的转变,即将化外变为大明的治内,使得这些瑶人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构成大明统治的基础。
殷正茂在奏疏中详细陈述了瑶乱的成因,由于这些被排除在里甲体系之外的瑶人在山林开下难以保证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往往造成经济纷争。而正统以来,广西贪腐之风日盛,瑶山内瑶承袭必须重贿,瑶人入籍之途亦被阻断。在此种形式下瑶山内瑶人入籍无路,又面临着官府压迫与剥削,掀起声势浩大的“瑶乱”。
再加上之前大量流民进入瑶人所在的山林,流民与瑶人有了共同的生活空间,并汇合成一股力量共同对抗官府,使得之前的徭乱呈现出屡征屡起的状态,现在要彻底平息徭乱,还两广以安宁,就必须要大举征讨,然后再重新建立秩序,不破不立,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对于朱载坖的态度,内阁已经麻了,他们很清楚朱载坖的想法,蒙古已经被按下去了,安南现在成为了朱载坖心中最大的隐患,安南之前的嚣张行为也使得朱载坖一直心中憋着一股气,准备好好爱一爱安南,在处理安南之前,自然是先要将云南和广西安顿好了再说,否则的话,朝廷出师安南,后路不稳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必须先在广西和云南将土司摆平了之后再收拾安南。
内阁当然是劝朱载坖稳一稳,毕竟朝廷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刚刚平定北虏,朝廷也需要休养生息。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