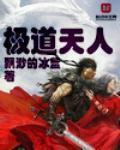趣书网>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书价 > 第157章(第1页)
第157章(第1页)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宪政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并不是法律专家的&ldo;非我莫入&rdo;的禁区。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法学院三年制的法学博士(jd)教育主要是一种法律职业训练,侧重于实用而非学术,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而法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则是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综合,比如,经济系在政府经济法规、产权制度、反托拉斯法、公司法等课题,政治系在美国宪法、司法制度、立法过程、政治法律思想等课题,社会学系在法律社会学、犯罪学、刑罚理论等课题,历史系在宪政历史、宪法史、法律思想史等课题,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由于英美普通法传统和案例教学法的影响,美国大学的法律教育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史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没有发达的法学教育,却有着庞大的法学学位获得者。我本人就是一个&ldo;法学&rdo;硕士。不过,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法学硕士学位(1985年),和绝大多数中国法学学位一样,并没有真正的&ldo;含法量&rdo;,因为我的专业学科是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而中国的学位分类中,包括党史和政治思想教育在内的所有政治学都属于法学范畴。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培养的&ldo;法学&rdo;学位获得者之多,大概连&ldo;诉讼之国&rdo;的美国都望尘莫及。
1988年,在师从杨生茂教授六年后,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了美国外交史方向的史学博士(博士论文后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题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随后南下金陵古城,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开始了我的职业学术生涯,一直为中心的美国学生讲授中美关系和国际冷战史,间或也给南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20世纪美国、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为促进中美两大民族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授课之余,利用中美中心丰富、精当和更新迅速的外文书刊,围绕着中美关系、中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一些学术研究和写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虽然成就不大,但自认为还算扎扎实实,研究工作开始有了驾轻就熟之感,一些研究成果也被同行学者所接受,用一句比较土的话来说,至少&ldo;混了个脸儿熟&rdo;。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对美国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9年夏初,南开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王正毅教授邀请我给&ldo;全球化和区域主义&rdo;国际讲习席班学员作一个有关国际体制作用的主题发言。为此,我特地撰写《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一文(后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在南开期间,我与正在南开历史所义务讲学的美国宾西法尼亚印第安纳(pennsylvaniadiana)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希博士邂逅相遇。承他不弃,送我一本他刚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回到南京后,我很快就读完这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对美国宪政的丰富内涵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是年夏天,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ldo;美国的世界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影响&rdo;为题的中美年轻学者对话会。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金灿荣博士也是与会代表。他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们同在美国所读研究生,我比他高两级,我学美国外交,他读美国政治,但后来他师从北京大学袁明教授攻博,转向了美国外交的研究。会余时间,我们漫步在电影&ldo;sleeplessseattle&rdo;(《西雅图夜未眠》《西雅图不眠夜》)中出现过的海滨码头,一起交流读王希书的体会,得出了同样的看法:美国宪政史和法治史在国内是个亟待开拓的领域,而且,美国人的宪政观和法治观对其外交的内在目标和外在行为方式都生产了重点影响。从美国人早期追求航海自由权、到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痴迷、到罗斯福的&ldo;四警察&rdo;观念(即二战后由美英中苏四大国像警察一样维持各自所在地区的国际安全和稳定)和联合国构想,再到当前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不遗余力的倡导和推动,无一不与其国内宪政观念和法治经验密切相关。显然,没有对美国宪政的一定理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和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评析是很难深入下去的。
这一考虑激活了我内心中对美国宪政法治的潜在兴趣。我过去对美国宪政一直有所注意,80年代初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给导师杨生茂教授写的第一篇读书报告就是《美国宪政史上的联邦法令废止权》(14年后,该文经大量修改后终于发表在《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1995年秋,根据自己在美国华盛顿的直接观感,为《读书》写了《在美国焚烧国旗是否合法?》(最近,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来信,告之他们将把该文编入日本的中文教材),随后,在研究美国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等弱势社会群体照顾性的&ldo;肯定性行动&rdo;计划时,更是涉及到不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民权案子。
2000年新学年开始,我毅然放弃了在前述&ldo;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rdo;一文基础后写作介绍美国&ldo;ultilateralis&rdo;(多边体制论,也译多边主义)的计划,开始了自己在美国宪政史的探索和冒险。遗憾的是,比较美国汗牛充栋的宪政文献,有价值的中文著述实在是少的可怜。除王希书外,余下的似乎只有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的《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与王希书按历史进程来讨论美国宪政的&ldo;史论&rdo;不同,该书按美国宪政的主要问题,对美国宪法原则进行了法理的分析。另外,台湾学者朱瑞祥写过一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史程》,以一系列案例穿起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