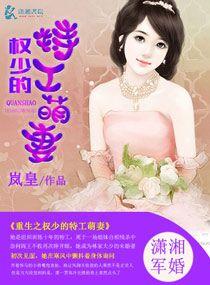趣书网>佐唐藩将重浑瑊读音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大唐会昌四年的春天,江南西道下辖的袁州,袁州治下的新吴县,新吴城中的百丈山,在熙熙攘攘的山道之上,有一人正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低头下山。
不理周围众人的挤撞,也无心欣赏眼前漫山的春光,崔向心中说不出来是何种滋味。半年以来,他缓慢而坚定地适应了唐朝,也接受了自己的新的身份和生活,却一直不敢前来离家中不过数里之遥的百丈寺,只因他心中始终有所担忧,一千一百六十六年之后的那四句偈语一直回荡在耳边。
今日终于鼓起勇气来百丈寺拜佛,也是半年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想刚一现身便被方丈识破身份。一番交谈下来,让他心乱如麻,匆匆下山而来,连事先前来百丈寺想要办的正事也忘到脑后。自己匆忙之中下山,到底是心有畏惧,还是心中担忧净贤长老会将他的秘密说出?
正心神不宁之时,忽见山道之上的众人纷乱起来,许多下山之人也纷纷转身向山上跑去,一时众人都是神色慌张,齐齐朝山上飞奔,不多时便传来隐隐的哭声。
一名小沙弥跌跌撞撞跑下山来,来到崔向面前,一脸悲容,哽咽说道:&ldo;方丈让我转告施主一句话。&rdo;
崔向心中闪过一丝不祥之感,忙问:&ldo;什么话?出了何事?&rdo;
&ldo;方丈说,且向西南行……&rdo;
小沙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再也忍不住心中悲痛,放声大哭:&ldo;方丈,方丈他……圆寂了!&rdo;
第二章崔家
崔向悚然而惊!
呆立半天,小沙弥早已返回百丈寺,得到了消息的善男信女们一片哭泣之声,崔向一动不动,又过了不知几时,他被寺中传来的钟声惊醒,这才朝百丈寺的方向长揖一躬,随后长袖一扬,飘然下山而去。
净贤长老是盘膝圆寂,正是修证到&ldo;坐脱立亡&rdo;的高僧大德于生死之上得大自在的灭度之法,况且长老非等崔向下山之后才盘坐解脱,其中寓意不言而明,便是让他安心离去,不必在意身后之事,也不用担心他的惊天秘密被人揭露。
崔向心中唏嘘不止。
他是凡人,自然不如高僧这般看破生死,虽说也因学佛知道一些清规戒律和佛教秘辛,不过他心中也是清楚得很,若不是净贤长老点破他的身份,犯了神通干涉定业的戒律,也不用必须圆寂。净贤长老之死并不能说全是因他而起,但至少也有他推脱不了的干系。
此生故彼生,其实还是因为他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秩序。若非他两世为人,净贤长老何必非要主动相见,提出让他保全百丈寺的不情之请。而长老又在看出他本来目的的情况下,本没有必要与他相见,也不用点破他的身份,以性命相求。
崔向心中喟叹,长老呀长老,你这又是何必呢?你明明知道我前来百丈寺的用心,本来也是为了救下百余名僧人早做准备,特意前来探察,你却还要拼了犯戒也要与我详谈,难道是看出了什么不成?
就算自己护全僧人是另有所图,但毕竟也有此心,长老此举,怕是另有深意?
&ldo;当、当、当……&rdo;
代表有高僧圆寂的十二响钟声传遍整个新吴,一时新吴城中一片哗然!
钟声辽远而广阔,声声直入人心,敲得崔向心中隐隐作痛。
回望远山之上的百丈寺,飞檐翘角、宝象庄严,崔向忽然下定了决心,他没有净贤长老生死自在的修为,却有知道历史走向的先机,出于私心也好,或是因为与百丈寺的渊源也罢,总得要不负净贤长老重托。男儿生于天地之间,总要有所担待,有所作为。
&ldo;且向西南行……&rdo;他低声念出这一句话,脚下却是奔走不停……
天近正午,崔向回到家中,推开院门,映入眼中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小院,占地约有十余丈方圆,有房屋七八间,其中正房三间,偏房四间。院中铺满青砖,间杂种有各种花草,生机盎然,尽管不过是独门独院,也不甚宽广,不过看来修整得平静整洁,青砖绿瓦,也算是富足人家。
父亲崔卓正在院中负手而立,一脸肃然,隐隐有一丝忧虑之色。
&ldo;父亲大人,孩儿回来了!&rdo;一见父亲,崔向立刻一脸恭敬,双手在胸前一叉,施礼说道。
崔卓正心事重重,正为是否前往袁州之事左右为难,归根到底,此事的症结还是在崔向身上,所以他一见崔向,便心中有气,重重地&ldo;哼&rdo;了一声:&ldo;不用心读书,跑到百丈寺所为何事?&rdo;
崔向对崔卓畏之如虎,忙道:&ldo;孩儿前去拜佛,求佛祖保佑,让孩儿智慧大增,也好不负父亲殷殷教导之心。&rdo;
崔卓与崔吴氏先是生了一子,名崔芦,幼年夭折。崔芦和崔卓一样,少时早慧,六岁便可做诗,被人称为神童,可惜七岁之时患病而死。崔向比崔芦小三岁,却是三岁时才会说话,十岁时还背不出《三字经》,十三岁时不会做诗,十六岁时,考了数次县学也没有考中,比起崔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直把崔卓气得七窍生烟,斥责他为&ldo;朽木不可雕也&rdo;。
崔卓心中清楚,崔向不是不肯用功,只是脑子笨,不是读书的材料,实在也是强求不得。只是他并不甘心,崔家一直是书香门第,虽说他并未高中进士,却一直以来不论县学、州学还是道学,都是超群绝伦之人,哪怕是死去的崔芦,也是少有才名,怎么偏偏就生出了崔向这样一个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