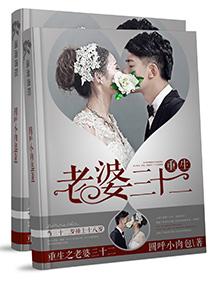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01章 数字公式录僖公三十一年(第4页)
第101章 数字公式录僖公三十一年(第4页)
与此同时,公子遂领命前往晋国。他身着鲁国最华美的礼服,带着大批珍贵的玉器、丝绸和骏马,浩浩荡荡奔赴晋国都城。此次出使,名义上是为了拜谢晋国赐予土地,实则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巩固鲁晋联盟,探听晋国对周边局势的态度。在晋国朝堂上,公子遂言辞恳切,态度谦卑,将鲁僖公的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晋襄公见状,龙颜大悦,不仅热情款待了公子遂一行,还承诺将继续维护鲁国的利益。
转眼间,夏日来临。四月的鲁国,本该是万物生长、生机勃勃的时节,然而鲁都曲阜的上空却笼罩着一层阴霾。鲁僖公一心想要通过盛大的郊祀大典,祈求上天保佑鲁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按照礼制,郊祀之前需进行占卜,以确定是否吉利。谁知,一连四次占卜,龟甲上的裂纹都呈现出不祥之兆。
太庙之中,气氛凝重。巫祝们手持龟甲,面色苍白,不敢言语。鲁僖公却不甘心就此放弃,他固执地认为,只要不杀祭祀用的牺牲,或许就能蒙混过关。于是,他下令停止郊祀仪式,却又执意要举行望祭。这一举动,在朝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大夫们纷纷进谏:“依礼,郊祀之礼,只需占卜所用之牛及祭祀之日是否吉利,牛一旦确定,便称‘牲’,不可再疑。如今既已确定了‘牲’,却又反复占卜郊祀吉凶,这是对祀典的怠慢,对神灵的不敬啊!更何况,望祭本是郊祀中的一个环节,如今郊祀不举行,望祭又有何意义?此举实乃不合礼制,恐遭天谴!”
然而,鲁僖公却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在他的坚持下,望祭仪式如期举行。祭坛之上,礼乐齐鸣,祭祀官员们身着庄重的礼服,向着东南西北三处方向虔诚跪拜,献上玉帛与美酒。可在场众人心中都明白,这不合礼制的祭祀,不仅无法求得神灵庇佑,反而可能会为鲁国招来灾祸。望着祭坛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许多人暗自叹息,一场危机,似乎正在悄然逼近……
眼见此情此景,在暗中围观这一切的普通之人王嘉,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寒风卷着祭坛上的灰烬掠过他的衣角,远处乐师们吹奏的埙声呜咽,仿佛也在为这场不合礼制的祭祀哀鸣。他望着鲁僖公固执的背影,忽然想起左丘明先生讲授的“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此刻看来,竟是如此讽刺。
紧接着,在长叹片刻之余,他便缓缓说出自己的反思思考与评价感悟来。“僖公此举,看似是对神明的虔诚,实则是对礼制的践踏。”王嘉的声音混着北风,带着几分震颤,“郊祀之礼,本是顺应天时、敬奉天命的大典,如今四次占卜不吉,分明是上天示警,可他却为了一己执念,强行举行望祭。这哪里是求福,分明是将鲁国置于险地!”
他望着祭坛上摇曳的烛火,思绪飘向济水以西那片新得的土地。“臧文仲大夫在分田时,尚能听从老者谏言,深知晋国之威不可违;公子遂出使晋国,亦懂得以谦卑之态巩固联盟。可僖公身为一国之君,却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王嘉攥紧了拳头,“若神明真的降罪,这片用结盟换来的土地,只怕也守不住啊!”
远处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王嘉裹紧衣衫,转身离去。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回响,如同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在这个寒夜,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命运,不仅系于疆土与盟约,更系于执政者对礼制的尊重与敬畏。而鲁僖公的刚愎自用,或许真的会成为鲁国祸端的开端。
紧接着,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转移…
秋,朔风卷着落叶掠过晋国的清原,枯黄的草甸上,数万甲士如林而立。晋文公身着玄色战甲,手持青铜令旗立于高台,身后旌旄猎猎作响。随着一声悠长的号角,三万六千匹战马同时昂首嘶鸣,扬起的尘烟遮蔽了半边天际。此番大阅,晋国将原有的上、中、下三军扩编为五军,新设新上军、新下军,军阵中战车列成雁形,步卒结成鱼丽之阵,铁甲寒光与戈矛锋芒交织,尽显霸主之威。“狄人屡犯边境,此番建五军,当教他们有来无回!”晋文公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军阵间回荡。赵衰立于诸将之中,因足智多谋且屡建奇功,被擢升为卿,当他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璋时,掌心沁出的汗意浸湿了冰冷的玉纹,深知这份荣耀背后是抵御外侮的千钧重担。
冬月,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鹅毛大雪,将卫国都城帝丘笼罩在一片苍茫之中。狄人的帐篷如黑色蚁群,密密麻麻布满城外的山岗,牛角号声与战马的嘶鸣彻夜不绝。卫成公蜷缩在厚重的貂裘中,听着城墙上传来的梆子声,面色惨白如纸。在迁都的第七日深夜,他忽梦到卫国先祖康叔怒目而视:“相夺走了我的祭品!”梦醒后,卫成公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祭祀夏朝帝王相。
次日清晨,宗庙前,青铜鼎中升腾的青烟裹着牲肉香气,却掩不住空气中的紧张气氛。宁武子疾步上前,袍角扫落石阶上的霜花,他长跪在地,声音里满是忧虑:“君上!鬼神只歆享同族的祭祀,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杞国、鄫国同为夏后氏后裔,都不曾祭祀相,足见不合礼制。相失去祭祀已久,并非卫国之过,怎可轻易违背成王、周公定下的祀典?”他叩首时,额头撞在青砖上发出闷响,“若随意更改祭祀,恐会触怒先祖,动摇国本啊!”卫成公皱着眉头来回踱步,袍袖扫翻案上的龟甲,最终却只是挥了挥手,示意继续祭祀。
与此同时,郑国新郑城内暗流涌动。公子瑕望着宫墙外低垂的乌云,心中满是不安。郑泄驾在朝堂上数次弹劾他结党营私,而郑文公本就生性多疑,近来更是对他横眉冷对。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惊雷炸响天际,公子瑕带着几名亲信,冒雨纵马狂奔。马蹄踏碎积水,溅起的水花混着泥浆,在他的衣袍上洇出深色痕迹。当楚国边境的烽火映入眼帘时,他勒住缰绳,回望郑国方向,只见闪电照亮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宛如一道撕裂故国的伤疤。而此刻的中原大地,狄人的战鼓、卫国的祭祀、郑国的内乱,正如同交织的蛛网,预示着新一轮的动荡即将席卷而来。
王嘉裹紧粗布棉衣,立于曲阜城头。朔风卷着清原阅兵的尘嚣、帝丘围城的呜咽,裹挟着新郑雨夜的惊雷,一同撞进他眼底。远处鲁国新垦的济水西田上,农夫们正顶着寒风翻整土地,木犁破开冻土的声响,竟与晋国战阵中兵器相击的铿锵隐隐共鸣。
“春秋无义战,诸国皆在刀刃上起舞啊……”他抚过城砖上斑驳的裂痕,仿佛触到了这个时代的累累伤痕。晋国扩军五军,名为御狄,实则暗藏争霸野心;卫国迁都祭祀,看似敬神,不过是君主病急乱投医的荒诞;郑国公子出逃,更显公室猜忌下的朝局糜烂。这些事件如同悬在中原上空的巨石,不知何时便会坠落,碾碎万千黎庶。
王嘉望着南飞的雁群,忽然想起左丘明先生讲过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如今祭祀乱礼,战事频仍,哪还有半点礼乐遗风?他又忆起臧文仲分田时的谨慎、公子遂使晋时的机变,这些周旋于强国间的智慧,在盲目自大的鲁僖公与昏聩的卫成公面前,竟显得如此无力。
“天道好还,不守礼制者,终会自食恶果。”王嘉的声音被北风扯碎,散入苍茫暮色。暮色中的中原大地,狄人的营帐如黑色毒瘤,郑国的烽火似血色残阳,而鲁国的望祭青烟仍在飘摇。他握紧腰间那卷《九章算术》竹简——那些丈量土地的公式、推演天时的算法,此刻竟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昭示着: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唯有以智慧为盾、以礼制为矛,方能在动荡中寻得一线生机。
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过后,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王嘉轻抚着冰凉的竹简,喉间滚动着干涩的吞咽,忽而低诵出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所言,不正是在警醒这些妄图以武力与疆土堆砌霸业的诸侯?”他的目光扫过天际翻滚的阴云,恍惚间,晋文公阅兵时的铁甲寒光与卫城墙上的皑皑白雪重叠,“可如今诸国恃强凌弱,弃礼义如敝履,又怎能不招致祸端?”
话音未落,他忽而又想起《道德经》中的字句,声调转为喟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晋侯扩军五军,口称御狄,实则贪欲如饕餮,终究是应了‘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的谶语。”寒风卷起他鬓角黑发,恍惚间,仿佛看见卫国百姓拖家带口迁徙的身影,听见稚子啼哭混着狄人战鼓的回响。
忽然,他攥紧竹简,声音中带着几分激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夫子周游列国,所求的大同之世,在这乱世中竟成了镜花水月!”他望着鲁国宗庙方向,那里的望祭青烟依旧袅袅,“臧文仲、公子遂尚知审时度势,可鲁侯却独断专行,这与墨子所言‘上不听治,下不从事’又有何异?”
最后,他的声音渐渐低沉,融入呼啸的北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后世之人,能从这些乱象中悟出治国安邦的真意……”说罢,他缓缓转身,身影逐渐消失在暮色中,只留下一句未尽的叹息,在城头的残阳里久久回荡。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在这之后不久,转眼间便进入了师生问答环节。
紧接着,他与他的那几个师哥师姐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
在此基础上,他又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有了更多的感悟。
这一天,很快也就过去了。
接下来,到了鲁僖公执政鲁国第三十二个年头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