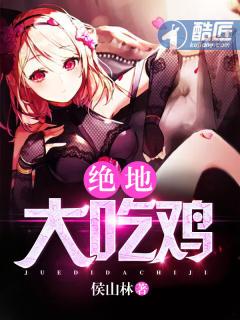趣书网>左传游记有哪些特色 > 第116章 专业特长观文公十三年(第1页)
第116章 专业特长观文公十三年(第1页)
专业特长,并非仅仅只是单纯局限于对某一领域天赋潜能的发掘与后天深耕细作的成果,它更是个体在历史长河中锚定自身价值的重要坐标。从本质而言,它是人类在认知世界、改造世界进程中,将与生俱来的禀赋与持之以恒的钻研相结合的智慧结晶。这种天赋优势犹如深埋地下的璞玉,需要通过个人苦心孤诣的钻研、夜以继日的修炼,方能雕琢出璀璨光芒;而支撑这一过程的,是个体追求杰出成就的坚定意志,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守,也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执着。
专业特长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始终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相连,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农耕文明时代,掌握农耕技术、手工技艺的匠人,凭借精湛的种植、纺织、冶炼等技能,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关键力量。他们的专业特长不仅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生存需求,还推动了陶器、青铜器等艺术形态的诞生,为文明传承奠定物质基础。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机械制造、化工冶炼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脱颖而出,他们以对蒸汽动力、精密仪器的深入研究,推动生产力飞跃式发展,重塑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在信息时代,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专业特长,成为驱动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的核心动力,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于社会生活层面,专业特长更是个体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依托。它不仅是获取物质财富、满足生活需要的手段,更是通往精神富足的桥梁。医生凭借精湛医术妙手回春,教师以渊博学识培育桃李,艺术家通过独特创意启迪心灵……这些专业特长的施展,既解决了社会的实际需求,也让从业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而那些在专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者,往往能够突破时代局限,以创新成果推动社会进步,如袁隆平毕生钻研杂交水稻技术,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问题;屠呦呦深耕中医药研究,成功提取青蒿素,挽救无数疟疾患者生命。他们的专业特长,早已超越个人成就范畴,升华为造福人类的伟大事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丰碑。
专业特长,从概念意义上讲,它是个体在特定领域经过长期系统学习、实践锤炼所形成的独特能力优势,是知识、技能与创造力的高度融合。这一概念既包含显性的专业知识储备与实操技能,也涵盖隐性的思维模式、创新意识和职业素养,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核心竞争力。从字面拆解,“专业”指向知识体系的专精与深入,强调对某一领域规律的系统把握;“特长”则突出个人特质与优势,彰显在同类能力中的独特价值。这种概念的界定,不仅勾勒出专业特长的外在边界,更揭示了其作为个体发展与社会分工重要纽带的本质属性。
当我们从深层内核与内涵研究时,我们对此也能够发现,专业特长绝非简单的技能堆砌,而是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它植根于人类对未知的探索欲望与生存发展需求,体现着个体对特定领域的深度热爱与执着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兴趣驱动与理性规划相互交织,天赋潜能与后天努力共同作用,逐渐形成具有独特个人印记的能力体系。从哲学层面看,专业特长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具体表现,通过在特定领域的深耕细作,个体将自身的意志、情感与创造力注入其中,实现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从社会学视角分析,它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产物,每个专业特长的存在都填补了社会运行中的特定需求缺口,共同构筑起复杂而有序的社会协作网络。
然而,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科技大师,对于专业特长技能能力的认识,呈现出多元而深邃的视角。孔子倡导“君子不器”,虽强调君子不应局限于单一技能,但同时也认可“六艺”专精的价值,认为专业特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支撑;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以游刃有余的技艺阐释了对专业领域的极致追求,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理念,揭示了专业特长与自然规律相契合的至高境界。西方世界中,亚里士多德横跨哲学、科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博学与专精的完美结合,他提出的“潜能与现实”理论,深刻剖析了专业特长从潜在能力到现实成就的转化过程。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的全才,在绘画、解剖学、工程学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他坚信不同专业领域间存在内在联系,倡导通过跨领域研究激发创新灵感。至近代,爱因斯坦以相对论革新物理学认知,同时强调想象力与音乐素养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打破了专业特长的单一维度认知,彰显了人文与科学交融的独特价值。这些大师的认知与实践,不仅拓宽了专业特长的内涵边界,更为后世在专业发展道路上提供了深远的启示与借鉴。
当我们回望人类社会漫长发展演进历史长河长卷,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古至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领域、军事战争军工业,还有文化艺术领域,在专业特长方面,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演变演进,在各行各业之中,无论是技巧技术,还是精巧细腻,亦或者是宛若科幻般的灵动无比和强大实力,以及在战争年代,救万千人民百姓与水火之中,以及在和平年代筑起“保家卫国”的和平长城,同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保障人们温饱生活基本问题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更多无限可能之举,都令人大家赞叹。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部落社会,人类便已凭借惊人的创造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黄河流域的仰韶先民将细腻的红陶土捏制成精美的人面鱼纹彩陶盆,用尖细的骨针在陶壁勾勒出灵动的游鱼与人面图案,每一道流畅的弧线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这些陶器不仅是实用的生活器具,更成为原始艺术与文化信仰的载体;长江下游的良渚部落则以硬度极高的燧石为工具,在玉器表面雕刻出繁密的神人兽面纹,线条细若发丝却刚劲流畅,将部落的图腾与精神信仰永久镌刻,同时,他们还建造起庞大的水利系统,通过堤坝、水坝和沟渠的巧妙组合,抵御洪水侵袭,保障农田灌溉,这一早期的水利工程智慧,为后世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孕育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同时期世界各国各文明的代表性文化遗址的洞穴岩壁画、石制玉制乃至早期青铜金属工具器皿,还有其他手工艺品中,处处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裴李岗人打磨的石磨盘与石磨棒,呈现出精确的弧形凹槽,将采集的谷物高效研磨成粉,这种原始的粮食加工工具,开启了人类从采集到农耕的伟大转变;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漆木碗,表面髹涂的朱红色生漆历经七千余年仍鲜艳如初,其精湛的髹漆技艺,不仅是实用功能的体现,更彰显出对美的追求与探索。
在遥远的欧洲,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的野牛岩画,采用天然矿物颜料,以透视与明暗对比手法,将野牛奔跑的动态与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岩壁上重叠的线条仿佛凝固了狩猎前的紧张气息;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受伤的野牛”,利用岩石的天然起伏塑造立体感,让观者仿佛能触摸到野牛肌肉的颤动。这些洞穴艺术不仅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创作,更承载着原始部落的狩猎仪式与精神信仰。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用黏土捏制出形态各异的滚筒印章,细密的楔形文字与神话图案环绕在神只周围,当印章在潮湿的泥板上滚动,便形成连贯的叙事画面,这不仅是权力与契约的象征,更是文字与艺术结合的雏形;古埃及人在涅伽达文化时期,已能用红铜锻造匕首与装饰品,刀刃上精心雕刻的蛇形纹饰,既体现了对尼罗河流域生物的观察,也暗示着王权与神性的融合。
而在美洲大陆,奥尔梅克文明的工匠雕琢出巨大的玄武岩头像,这些高约3米的巨石头戴古怪头盔,面部表情威严庄重,石像表面打磨得光滑如镜,在热带雨林的阳光下泛着神秘的光泽,其雕刻工艺与运输技术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安第斯山脉的查文文化中,黄金匠人们运用“失蜡法”制作的鸟兽形吊坠,羽毛与鳞片的细节栩栩如生,黄金特有的光泽与宗教仪式相结合,成为沟通人与神灵的媒介。
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文化瑰宝,虽诞生于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社会背景,却共同勾勒出人类文明起源的壮丽图景。从粗糙的石器到精美的玉器,从简单的岩画到复杂的金属工艺,每一件手工艺品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它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物质遗产,更传承着古老而坚韧的文化基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紧接着,伴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工具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当人类社会逐渐脱离野蛮时代,逐步朝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发展演进时,在中国、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对于专业特长领域,无论是农牧业、手工业、文化艺术业、军事工业类、民生民事类,还是基础设施建造类和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大领域,对于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还有独具创造性的有利想象力,创新性特长的认识,都在雏形和后续不断发展演进过程中,不断向前迈进,而且也为后世奠定了十分深厚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雨后春笋一样规模庞大且数量众多的专业领域着作典籍和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时代浪潮下,这些认知内容的价值体现,也无不生动的展现出来。
在中国,早在夏商西周时期,青铜铸造业已发展至巅峰,成为奴隶制社会权力与文明的象征。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需八百余人协同作业方能完成铸造,鼎身饕餮纹的狞厉线条、云雷纹的繁复回环,不仅彰显着工匠对造型艺术的精准把握,更暗含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宗教图腾崇拜。西周时期的“百工制度”将手工业者编入世袭户籍,制玉匠以“解玉砂”雕琢出的龙凤玉佩,线条婉转如流水,谷纹颗粒饱满,每件器物都严格遵循《考工记》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法则,将自然、材质与技艺完美融合。
农业领域,西周推行的井田制以规整的沟渠系统划分土地,《诗经·豳风》中“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的记载,展现出先民对农耕时序的精确认知。灌溉工具“桔槔”的发明,利用杠杆原理汲水,使农田摆脱对天然水源的依赖;而“耦耕”技术的普及,让两人协同耕地效率倍增,这些技术革新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奴隶制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艺术方面,商代的甲骨文刻写已形成成熟的文字系统,卜辞中对天象、祭祀的记载,既是宗教活动的记录,也是早期文学创作的雏形。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将艺术与政治深度绑定,编钟的铸造严格遵循音律规范,曾侯乙编钟的65件钟体可演奏五个八度的乐曲,每个钟面的双音设计更是声学奇迹。《周礼·春官》中详细记载的“大司乐”教育体系,将“乐德”“乐语”“乐舞”纳入贵族教育,使艺术成为维护等级秩序的重要工具。
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商代已出现青铜戈、矛等兵器,戈援与戈内的夹角经过反复测算,确保在车战中既能钩杀又能啄击;西周时期的“车战”战术成熟,四马战车的制造需经过三十余道工序,辀、舆、轮的尺寸严格符合《考工记》标准,车轴两端的青铜軎饰不仅具有装饰性,更能增强车轴的耐用性。这些军事技术的进步,使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得以贯彻,为王朝的扩张与稳定提供了保障。
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展现出惊人的规划能力。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群,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廊庑、庭院、殿堂的设计彰显着王权威严;西周的道路系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路两旁种植行道树,兼具交通与礼仪功能。这些建筑实践不仅体现了高超的工程技术,更蕴含着“居中而治”的政治哲学,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营造树立了典范。这些早期的文明成果,如同基石般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大厦,其蕴含的智慧与创造力,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光芒。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生产力变革的大门。铸铁柔化处理技术的突破,让农具兼具硬度与韧性,犁铧翻土更深,铁镰收割更利,“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景象渐成常态。都江堰水利工程横空出世,李冰父子以“深淘滩,低作堰”的智慧,将岷江之水化作滋养成都平原的甘霖,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精妙设计,使蜀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
手工业领域迎来百家争鸣的繁荣。齐国的《考工记》系统总结“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将工艺标准精确到尺寸与比例;吴越之地的铸剑师欧冶子,以“雨师扫洒,雷公击橐”的气势,锻造出“龙渊”“泰阿”等名剑,剑身的菱形暗纹经硫化处理,历经千年仍寒光凛冽。漆器工艺更是达到新高度,楚国工匠以数十道髹漆工序打造的虎座凤架鼓,朱红与黑色交织的云纹流转如火焰,昂首的凤鸟与伏卧的猛虎构成极具张力的造型,将实用与艺术完美融合。
思想文化领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空前绝后。孔子编订《诗》《书》《礼》《乐》,以“仁”“礼”为核心构建儒家学说,其弟子整理的《论语》以简洁隽永的对话体,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老子的《道德经》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辩证思维,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终极奥秘;墨子在《墨经》中记载的小孔成像实验,比西方早了百余年,其对杠杆原理、滑轮应用的论述,展现出卓越的科学洞察力。这些经典着作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军事领域的变革同样惊心动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弃宽袍大袖而着短衣皮靴,改车战为骑战,让赵国骑兵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孙武所着《孙子兵法》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战略思想,系统阐述战争规律,其“兵者,诡道也”的论断,至今仍是军事理论的圭臬。此时的兵器制造更加精良,三棱青铜箭镞的流线型设计减少空气阻力,其锐利程度可穿透三层牛皮甲;弩机的改良使箭矢射程翻倍,望山瞄准装置的出现,标志着冷兵器向精准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城市建设与民生工程也呈现新气象。齐国都城临淄“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其城市规划已出现明确的功能分区,手工业区、商业区与居住区错落有致;郑国子产“铸刑鼎”,将法律条文镌刻于青铜鼎上,开启了成文法公开化的先河,保障民生民事有法可依。这些变革与创新,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剧烈转型,更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崛起积蓄了磅礴力量,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为各领域的发展注入磅礴动力,华夏文明在制度整合与技术革新中迈向新的高度。秦始皇以“车同轨,书同文”的魄力,修筑起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网络,宽阔的道路上铺以夯土与砂砾,道旁栽植青松形成林荫,其主干道“直道”从云阳直达九原,全长千八百里,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更为商业流通与文化传播开辟通途。灵渠的开凿堪称水利工程奇迹,工匠们以铧嘴分水、陡门调节水位,将湘江与漓江连为一体,使秦军得以顺利南征百越,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运河,至今仍滋养着岭南大地。
农业生产在铁犁牛耕普及的基础上迎来技术飞跃。赵过推广的耦犁与耧车成为农耕神器,前者由二牛三人操作,犁壁可翻土碎垡,后者三腿耧一次能播三行种子,日均播种一顷,效率远超人力点播。代田法与区田法的出现,将土地耕作与肥力保持推向科学化,“一亩三甽,岁代处之”的轮作模式,有效提升了粮食产量。汉代的温室栽培技术更是令人惊叹,宫廷园圃中以“屋庑”覆盖蔬菜,“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在寒冬腊月培育出葱、韭等鲜蔬,展现出古人对农业环境的主动调控能力。
手工业领域,冶铁业的发展达到新巅峰。南阳太守杜诗发明水排,以水力驱动皮囊鼓风,使冶铁炉温大幅提升,铸铁脱碳钢与炒钢技术的成熟,让兵器与农具的质量实现质的飞跃。山东临淄的铜镜工坊,匠人以“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装饰镜面,采用“汞齐法”镀锡,使铜镜光洁如银;蜀地的织锦业独步天下,成都织工以蜀锦机织出的“汉并天下”锦,经锦纬彩,纹样中祥禽瑞兽栩栩如生,一匹蜀锦价值“数金”,远销中亚与罗马。
文化艺术领域,汉代学者对典籍的整理与传承居功至伟。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的皇家校书工程,将先秦古籍分类编目,形成《七略》这一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着成《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例,为后世史学树立典范。艺术创作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以“因材施艺”闻名,巨大的花岗岩经寥寥数凿,便化作“马踏匈奴”的雄浑造型,原石的天然纹理与粗犷线条,尽显大汉气象;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以浪漫诡谲的神话场景描绘升天图景,朱砂、石青等矿物颜料历经千年仍鲜艳夺目,其“t”形构图与分层叙事,开创了中国绘画的独特范式。
军事工业的进步助力汉帝国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的武库已实现标准化生产,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箭镞,经检测发现其化学成分与形制规格高度统一,三棱箭镞的流线型设计符合空气动力学,强弩的拉力可达十石,射程超过六百步。汉军的铠甲制作更为精良,“玄甲”以铁甲片编缀而成,胸背处的甲片细密如鱼鳞,既能防护要害,又不影响作战灵活性。这些军事技术的革新,让卫青、霍去病的铁骑得以深入漠北,封狼居胥,将汉帝国的版图推向辽阔的西域。
民生民事领域,汉代的“常平仓”制度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保障。丰年时官府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灾年则低价抛售,“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有效平抑物价、赈济灾民。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九章律》在《法经》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对田赋、徭役、户籍等民生事务作出详细规定,为“文景之治”与“光武中兴”的盛世奠定法治根基。这些成就共同构筑起秦汉文明的宏伟大厦,其制度框架、技术体系与文化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世两千年的历史进程。
随后,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但在动荡的岁月里,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力依然迸发出璀璨光芒,各领域在碰撞与融合中孕育着新的突破。这一时期,民族大迁徙与文化大交融成为时代主调,为专业特长的发展注入了多元活力。
在农牧业领域,北方游牧民族的畜牧经验与中原农耕技术相互借鉴。贾思勰所着的《齐民要术》堪称农业百科全书,系统总结了选种育种、土壤改良、轮作套种等技术,其中记载的“踏粪法”利用牲畜粪便发酵制肥,显着提升土壤肥力;“嫁接术”则巧妙地将不同植物的优良性状结合,培育出高产果树品种。南方地区因人口南迁带来先进工具,翻车(龙骨水车)被广泛应用于水田灌溉,其木质链条与叶片组成的汲水系统,可连续将水提升至高处,使江南“湖田”得以大规模开垦,为日后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基础。
手工业呈现出地域特色鲜明的繁荣景象。灌钢法的发明革新了冶铁技术,工匠将生铁与熟铁按比例混杂加热,反复锻打,使碳元素均匀分布,打造出的钢刀“斩甲过三十札”,锋利无比。丝绸织造在继承汉代技艺的基础上融入西域纹样,波斯风格的联珠纹、忍冬纹与传统云气纹交织,在蜀锦、云锦中绽放出新的魅力。制瓷业更是取得突破性进展,浙江越窑的青瓷采用龙窑高温烧制,釉色“类玉似冰”,其秘色瓷的釉料配方与烧制工艺堪称一绝;北方的白瓷烧制技术也逐渐成熟,胎质细腻、釉色纯净,为后世青花瓷的诞生埋下伏笔。
文化艺术领域,思想的碰撞催生了多元繁荣。佛教东传与本土儒道思想交融,玄奘西行取经带回大量梵文经典,佛教石窟艺术在各地兴起。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匠人们以凿子为笔,在石壁上雕刻出千佛万像,云冈石窟第20窟的露天大佛,高13。7米,面部轮廓雄浑大气,衣褶线条流畅,既有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子,又融入中原审美;龙门石窟的“龙门二十品”书法作品,字体刚健质朴,是魏碑书法的典范。文学领域,陶渊明的田园诗以自然恬淡的笔触描绘农耕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影响后世千年;南北朝民歌南北风格迥异,北方《木兰诗》塑造了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形象,南方《西洲曲》则以细腻婉约的笔触书写相思之情,共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形式。
军事工业在频繁的战争中加速革新。马镫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骑兵作战方式,这种看似简单的金属脚踏装置,使骑手在马上的稳定性与冲击力倍增,骑兵得以发挥更大威力。攻城器械不断升级,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钩车”“冲车”“拍竿”等,其中拍竿以杠杆原理将巨石抛向城墙,破坏力惊人;水战中,南朝的“楼船”高达十余丈,船上可容纳数千士兵,装备拍竿、弩炮等武器,成为水上移动堡垒。
民生民事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艰难中前行。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按人口分配土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北周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强调“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等施政理念,为地方治理提供指导。城市建设方面,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人口百万,“市廛列肆,埒于二京”,秦淮河两岸商铺林立,其城市规划突破传统里坊制,商业活动更加自由。而在水利方面,寿春的芍陂经过历代修缮,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支撑江淮地区经济的重要水利工程。
这一时期,尽管政权割据、战火纷飞,但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融合,为专业特长领域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无论是农牧业的精耕细作、手工业的匠心独运,还是文化艺术的多元创新、军事技术的实战突破,都为隋唐时期的全面繁荣积累了深厚底蕴,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过渡篇章。
而在隋唐时期,大一统格局与开放包容的国策,将中华文明推向全新高度。这一时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如巨龙横卧华夏,工匠们以“堰埭”调节水位,用“纤道”辅助航运,将黄河、淮河、长江水系连为一体。“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漕运盛况背后,是“邢窑白瓷、越窑青瓷装船南下,苏杭丝绸、扬州漆器溯流北上”的经济繁荣。曲辕犁在江东地区应运而生,其犁评、犁箭的调节装置,使深耕浅种皆可自如,配合筒车“随流自转,日灌百亩”的自动汲水系统,让江南水田真正成为“一岁再获,仓廪充实”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