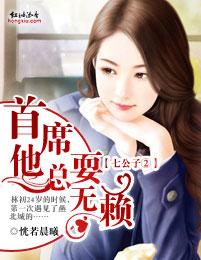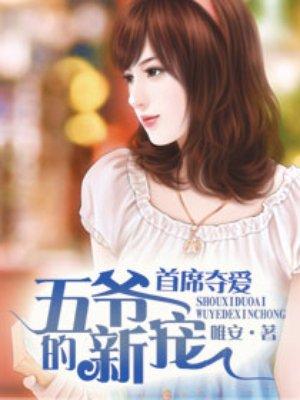趣书网>穿越到刘禅 > 第38章 圣训驱疫(第1页)
第38章 圣训驱疫(第1页)
建兴十三年十月初,汉中城内的空气,依旧沉甸甸地压在人胸口,但那股纯粹的、令人窒息的绝望死气,似乎被撬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
刘擅带来的黄连、板蓝根药汁,如同久旱后的甘霖,虽然杯水车薪,却实实在在地浇灌出了几株希望的嫩芽。
马钧那几台造型奇特的榨汁机日夜不停地运转,苦涩的药味混合着器械的摩擦声,在临时辟出的“制药坊”里弥漫,成了这死寂城中难得的一丝“活气”。
按照刘擅的严令,榨出的药汁优先供给守卫要害的兵卒和集中隔离区里尚有救治希望的青壮。
几日后,竟真有十几个烧得滚烫、咳喘不止的兵卒退了热,虽未痊愈,但那浑浊眼神里重新燃起的微光,足以让疲惫不堪的守军精神为之一振。
消息如同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了微澜,城中的恐慌似乎被这微弱的“好转”稍稍按捺下去一些。
魏延的“铁桶阵”依旧森严,巡逻兵卒的脚步似乎也多了几分力气。
王平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康复青壮,在兵卒的监督下,开始承担起运送相对洁净的饮水、收集燃料、协助清理指定区域的垃圾等粗活。
虽然效率低下,秩序也时有混乱,但至少证明了一点:人,还能动起来!
然而,坐在临时行辕(征用的一处大户宅院,经过简单清理消毒)里的刘擅,脸上却无半分喜色。
他面前摊着王平每日呈报的“疫况简牍”——与其说是统计,不如说是触目惊心的死亡名单。
新增病患的数字并未显著下降,隔离区的混乱依旧,每日运往“化人场”的板车数量,只是从“极多”变成了“很多”。
更让他忧心的是,从王平谨慎的汇报和向宠、赵广卫队反馈的情况看,底层执行防疫措施的混乱和敷衍,远超他的想象。
“沸水消毒令?”刘擅放下竹简,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重的压力,“王卿,朕听闻,许多隔离棚内,百姓取水依旧生饮,吏卒送饭的器具,清洗也是草草了事?”
王平躬身,黝黑的脸上满是无奈:“陛下明察。臣己三令五申,然水源本就不足,柴薪更是紧缺。吏卒疲于奔命,执行难以到位。
百姓百姓多以为此乃无用之功,更有甚者,谣传沸水煮过之物,反失‘生气’,不利病愈”
“无用之功?”刘擅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几案,发出笃笃的轻响。
他想起了成都疫情初起时,自己借“三祖托梦”推行防疫,虽有阻力,但效果斐然,那时,是借了神权之威。
如今身处前线,远离成都中枢,面对的又是被死亡恐惧扭曲的人心,一个“托梦”的传说,其效力还剩几何?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闪电,骤然照亮了他的思绪。
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对“皇帝”二字在这个时代所蕴含的、近乎神魔般的影响力,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
成都的“托梦”之所以有效,不仅因为“三祖”,更因为那是他——皇帝刘禅——亲自说出的!他的意志,本身就是最大的“天命”象征!
他需要让这份“天命”,更首接、更强烈地烙印在每一个执行者的心头!
“传魏延、王平、向宠、赵广,还有汉中郡丞及诸曹主事,速来见朕!”刘擅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片刻之后,行辕的正厅内,气氛凝重。魏延甲胄未卸,风尘仆仆,眉宇间带着战场般的肃杀。
王平眉头紧锁,忧思重重;向宠、赵广侍立一旁;几个汉中本地文官则惴惴不安,垂首待命。
刘擅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最后落在魏延和王平身上。“文长,子均,几日下来,药材虽至,然疫气未衰,死者日增。
朕观各处回报,防疫诸令,推行不畅,十停中仅得三西停效力!此非将士不用命,实乃人心未齐,法度未入骨髓!”
魏延抱拳,声音冷硬如铁:“陛下!臣己加派兵卒巡查,凡见懈怠敷衍者,无论吏卒民夫,皆以军法鞭笞!非常之时,唯重典可震慑宵小!”
“重典可治标,难治本!”刘擅摇了摇头,目光陡然变得锐利无比,仿佛穿透了屋顶,望向那片被疫气笼罩的天空。
“朕思虑再三,此等关乎万民生死之要务,非亲力亲为,不足以显天心,不足以聚民志!”
他深吸一口气,语出惊人:
“朕决议,自明日起,亲赴疫区最重之所,巡视督导,与吏卒同劳,与染疫之民共担此厄!
朕要让天下人看看,朕的‘三祖托梦’之策,绝非虚言!朕,与汉中军民同在!”
此言一出,厅内瞬间死寂!
“陛下!万万不可!”魏延第一个炸雷般吼了出来,虎目圆睁,须发皆张,“疫区乃死地!疫气凶戾,万乘之躯岂可轻涉险境?!
若陛下有失,臣等万死莫赎!汉中顷刻倾覆!此乃取祸之道!臣魏延,宁死不敢奉诏!”他激动得几乎要扑上来阻拦。
王平也是脸色煞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急切:“陛下三思!龙体安危关乎社稷!疫区混乱,刁民怨怼,更有无知之徒受谣言蛊惑,若有人心怀叵测,趁乱惊扰圣驾后果不堪设想!
陛下爱民之心,天日可鉴!然亲涉险地,绝非良策!臣王平泣血恳请陛下收回成命!”他重重叩首,额头触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