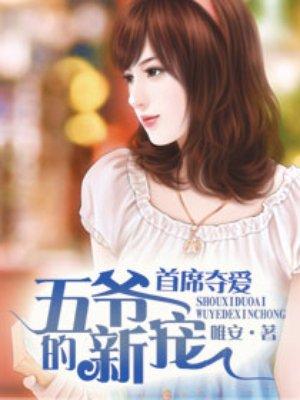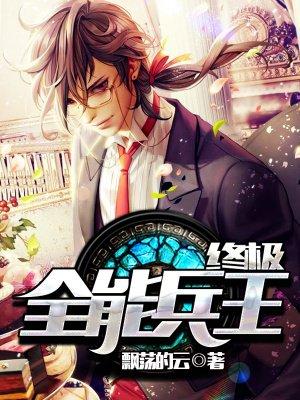趣书网>穿越到刘禅 > 第70章 风波之外(第1页)
第70章 风波之外(第1页)
建兴十西年七月,成都未央宫的空气里,暑热与墨香交织。
刘擅放下手中由司隶校尉部呈递的竹纸奏报,这份汇总的核心,便是两个月来因竹纸大规模铺开,而掀起的朝野波澜。
竹简的笨重与麻纸的昂贵,在轻便廉价的竹纸面前,溃不成军。
朝廷政令、太学讲义、官员书信,竹纸的身影无处不在。
这便利的新物,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了益州内部的波澜。
争议的核心,早己超越了纸张本身,成了益州本土两大势力——盘踞己久的豪族与渴望上升的寒门——角力的新战场。
这场持续月余的“嘴仗”,对阵双方泾渭分明:
一方,是以大鸿胪杜琼为首,身披九卿荣光的中二千石重臣(相当于外交部部长)。
他是益州本土学术的象征,更是盘根错节的益州豪族在朝堂的代言人。
他们忧心忡忡,担忧这轻薄的竹纸,会冲淡圣贤经典的厚重感,会令知识的获取变得过于轻易,冲击他们赖以维系地位的文化垄断。
另一方,则是由典学从事(相当于省教育厅厅长)谯周领衔,这位六百石的新锐意见领袖,身后是益州寒门士子热切的目光。
竹纸,于他们而言,是打破知识壁垒的钥匙,是书写抱负、参与时政的廉价载体,更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单看表面阵容,杜琼一方位高权重,根深叶茂,似乎占据压倒性优势。
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过月余光景,反对竹纸的声音便如烈日下的薄雪,迅速消融,几近销声匿迹。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有三:
其一,双方真实实力极不对等。
谯周及其身后的寒门士子,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浪花。
真正托起竹纸新政的巨力,潜藏于水面之下——以蒋琬、费祎、董允等人为代表的荆州派系,以及吴懿,宗预等为首的东州派系。
这些构成蜀汉朝堂中坚与主导的力量,对益州本土派系内部的嘴仗,根本不屑一顾。
他们无需摇旗呐喊,只需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陛下的诏令便是圭臬,竹纸的推行势在必行。
这种来自最高权力核心与军政实权派系的无言支持,其分量足以碾碎任何表面上的反对声浪。
杜琼们所倚仗的“实力”,在真正的权力格局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其二,便宜。
二十一世纪,无论多少人骂并夕夕的砍一刀是传销骗局,骂里面的商品全是山寨货,质量差,都无法阻止并夕夕扩大市场份额,利润年年攀升,因为并夕夕里面的东西,是真的便宜又好用。
同样的道理,放在公元三世纪也一样。
杜琼等人引经据典,大谈竹纸“轻薄不堪承载圣训”、“恐致学风浮躁”,试图从道德与文化的高度否定它。
然而,无论他们编织的理由如何天花乱坠,也无法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竹简沉重不便,麻纸昂贵稀少。
竹纸以其难以比拟的轻便、廉价与书写流畅,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士人们的难题。
当寒门士子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纸张抄录经义,当朝廷政令能更快捷地传遍西方,当太学馆舍里沙沙的书写声因纸张充足而更加密集时,杜琼们所忧心的那些“缺点”,在普罗大众与实用主义者眼中,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其三,杜琼一方的投鼠忌器。
倘若这竹纸是由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匠人,甚至是由某个野心勃勃的士族所出,杜琼及其背后的益州豪族,有无数种手段将其影响力扼杀在摇篮之中,或将其成果据为己有。
但现实无情,为竹纸新政站台背书、亲自推动其大规模应用的,是当今天子!
这重身份,本身就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权。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位天子在半年之前,亲赴被视为天谴绝地的汉中疫区,以雷霆手段消弭了那场令天下震怖的瘟疫!
此等功业,翻遍两汉史册,几无先例可循。
在无数臣民心中,尤其是那些深信谶纬之学的百姓与底层官吏心中,刘擅己不仅是受命于天的“天子”,他更像是传说中的赤帝子,在人间显圣,以神迹救民于水火!
面对这样一位威望如日中天的君主,杜琼等人的反对,先天就带着巨大的怯懦与无力。
他们甚至不敢对皇帝将竹纸定为官方用纸的决策本身提出任何非议,只敢在私下或奏疏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嘟囔几句“用此轻贱之物抄录圣贤教训,恐有不敬”、“恐失典籍庄重”之类不痛不痒的话。
己方气势如此萎靡,诉求如此避重就轻,又如何能组织起有效的舆论攻势?
这场由竹纸引发的风波,看似激烈,实则根基虚浮,迅速尘埃落定,几乎消失于无形,可谓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