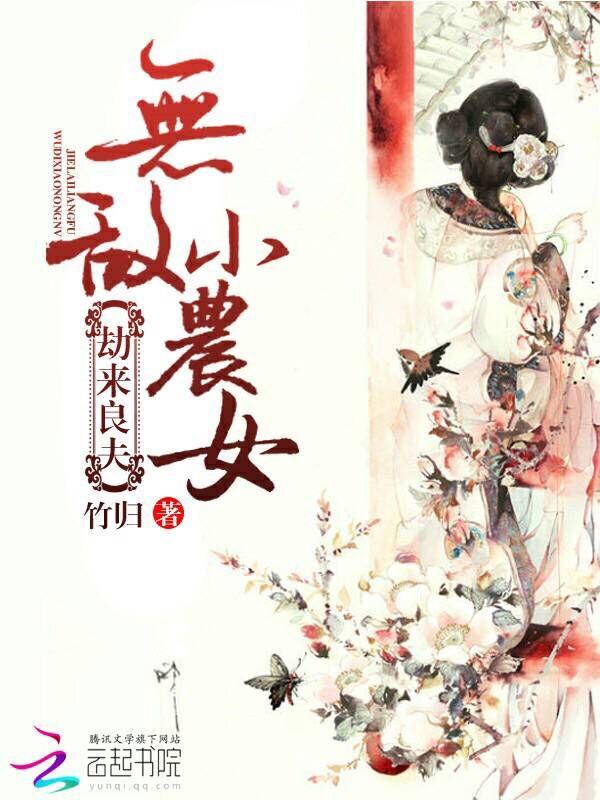趣书网>官路芬芳 > 第1104章 夜色温情几度春潮(第1页)
第1104章 夜色温情几度春潮(第1页)
夜色如浓稠的墨砚,将3号别墅晕染得只剩窗棂间漏出的几缕暖黄。
朱飞扬推开卧室门时,走廊里的壁灯正散着朦胧的光晕,地毯吸走了他所有的脚步声,唯有鼻尖还萦绕着蒋灵韵丝间的栀子花香——那是她下午刚洗过头,用的是城南老字号的香膏,混着她颈间淡淡的奶香,成了此刻最勾人的余韵。
卧室里的薄绒被陷出一个温柔的弧度,蒋灵韵的睡颜在月光下泛着瓷白的光泽。
她的睫毛很长,此刻像受惊的蝶翼轻轻颤动,嘴角还带着未褪的潮红。
朱飞扬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指尖触到她裸露在外的肩头,温热的触感让他喉结微动——方才她趴在锦被上喘息时,这处肌肤曾泛起过细密的汗珠,被他用吻一点点吻干,留下一串细碎的红痕,像雪地里绽开的红梅。
他记得她最后瘫软在他怀里时,声音软得像化开的蜜糖:“飞扬,你去楼下吧,龙凤胎半夜要是哭了,你叫醒我……”
话没说完就被他咬着耳垂打断,此刻那些缠绵的余温还残留在被褥间,混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甜腥气,成了这场温存的注脚。
楼下的走廊转个弯就是青儿的房间。
门是虚掩着的,门缝里漏出的灯光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光带,像一道无声的邀约。
朱飞扬推开门时,正看见青儿趴在床沿的手猛地蜷缩了一下——她果然没睡。
月光从纱帘缝隙里溜进来,在她光滑的脊背上游走,那道从肩胛骨延伸到腰线的曲线,曾被他无数次描摹过,此刻在阴影里更显柔韧,像一尾等待入水的鱼。
“师叔。”
青儿的声音带着刻意压抑的颤抖,当朱飞扬掀开被子躺进去时,她像只受惊的小兽猛地缩进他怀里。
她的皮肤比蒋灵韵更凉些,像刚从溪水里捞出来的玉,指尖却烫得惊人,攥着他睡衣的布料不肯松开。
朱飞扬闻到她间的薄荷香,那是她常年练剑留下的习惯,总爱用清爽的草药肥皂,可此刻这清冽的气息却被她急促的呼吸熏得烫,混着她胸前若有若无的奶香——那是白日里给龙凤胎喂奶时沾染上的,竟成了最撩人的催化剂。
青儿的吻带着青涩的莽撞,牙齿偶尔会磕到他的唇角,却又在下一秒用舌尖小心翼翼地舔舐,像只笨拙的小猫在讨好主人。
她的指甲陷在他后背的肌肉里,留下几道浅浅的红痕,当他托着她的腰让她更贴近自己时,她忽然出一声细碎的呜咽,泪水砸在他的锁骨上,烫得他心头一紧。“师叔,我想你……”
这五个字被她反复呢喃,从最初的羞涩到后来的忘情,声音里的渴望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将两人都拖进翻涌的浪潮里。
月光在床尾的地毯上移动,映出交缠的影子,像幅流动的水墨画,直到窗棂透进第一缕鱼肚白,青儿才带着满足睡去,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
朱飞扬起身时,青儿的手臂还松松地环着他的腰。
他掰开她的手指,指尖触到她掌心的薄茧——那是常年握剑磨出的,在柔软的肌肤上格外清晰。
刚走到门口,身后忽然传来窸窣声,回头便看见青儿半睁着眼。
脸颊泛着红晕:“师叔,天亮了……”她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目光却亮得像含着星子,“我去给你打盆热水。”
洗手间里很快传来水声。
朱飞扬正对着镜子整理衣襟,忽然听见身后两道极轻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