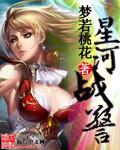趣书网>Furry:弘阳国皇子 > 第71章 江映蓉(第2页)
第71章 江映蓉(第2页)
江明镜捧着新印的《弘阳通鉴》走来,补充道:&0t;姑姑,寒鸦渡的海棠结果了,守军说甜得很。&0t;他翻开史书某页,那里新添的小注记载着:永和二年,女帝令盐税三成直接拨付当地学堂。
雨停了,宫人抬来江映蓉幼时用过的算盘。她随手拨弄,珠子竟排成&0t;天下为公&0t;四字。远处传来孩童的读书声,念的正是新政颁布的《盐铁平价诏》。
(终)
尾声青霄月
永和三年的上元节,月影城的灯会比往年热闹了三成。江映蓉站在城楼上,看着朱雀大街上穿梭的商贩——卖糖画的老汉举着新做的算盘样式糖人,穿绿袄的小姑娘正给母亲读着墙上张贴的《盐铁平价诏》。
“姑姑,您看那边。”江娇楚指向街角,江明镜正蹲在灯笼下,给一群孩童讲《弘阳通鉴》里“女帝扮商查盐案”的故事。青年史官的声音混在猜灯谜的笑闹里,竟比戏楼的唱词还动人。
6沉捧着个锦盒走来,里面是修复好的半张《盐铁新策》。墨迹历经三世风雨,“迎涵手书”四个字却依旧清晰。“寒鸦渡的海棠树开花了,”他低声道,“百姓在树下建了座小祠,说那是‘续志祠’。”
江映蓉忽然想起1209年的那个雪夜,刚出生的江迎涵被父亲抱在青霄殿,窗外是大哥江平德送来的海棠盆栽;又想起1303年弥留之际,九旬的自己摸着江明镜的胎,说“要让天下人都吃得起盐”;最后落在1320年的江府账房,柳絮落在砚台上,她正算着北地皮毛的利钱,心里却莫名记挂着月影城的粮价。
远处传来报时的钟声,十二响过后,新铸的“永和通宝”在灯影里泛着暖光。江映蓉从袖中取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三粒海棠种——一粒采自青霄殿遗址,一粒来自寒鸦渡,最后一粒,是昨夜江明镜从落鹰峡带回的。
“去把它们种在太庙旁吧。”她将布包递给6沉,指尖拂过城砖上的斑驳痕迹,那里不知何时被风雨冲刷出个模糊的“涵”字。
江娇楚忽然指着天空:“姑姑,您看那轮月亮!”
圆月正悬在青霄殿旧址的方向,清辉漫过宫墙,漫过朱雀大街,漫过每个挑着灯笼回家的百姓肩头。江映蓉笑了,想起当江映蓉时,父亲总说“经商要像月亮,不夺日光,却能照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或许轮回从不是为了重复,而是让每一世的微光,终于能连成照亮前路的星河。就像此刻,账本上的数字、奏折上的朱批、孩童口中的故事,还有那粒正埋入泥土的海棠种,都在说着同一件事——
江山代续,而民心,是永不褪色的传承。
最终章长明灯
永和五年的春分,江映蓉在太庙前栽下的三株海棠已亭亭如盖。她站在树下,指尖抚过树干上刻着的三道年轮——青霄殿、寒鸦渡、落鹰峡,三世的记忆最终化作树影婆娑。
6沉捧着一盏长明灯走来,灯芯是用《盐铁新策》的残页卷成的,火光映着纸上未褪的墨迹。江映蓉接过灯,轻声道:“该熄了。”
可当她抬手欲掩时,灯焰却骤然一盛,火光中浮现出无数细碎的画面——
-第一世,江迎涵在青霄殿的雪夜写下《盐法初议》,墨迹未干便被大哥江平德派人截下;
-第二世,三公主在流亡途中将改良盐政的密信缝进冬衣,托商队带回都城;
-第三世,江映蓉在账房里拨着算盘,无意间算出了与前世相同的盐税亏空比例……
原来那些未竟的志向,从未真正熄灭。
灯焰渐弱时,江明镜匆匆跑来,手里捧着一封北境急报:“姑姑,边关互市新到了一批西域琉璃灯,商人们说……灯罩上刻着‘涵’字。”
江映蓉一怔,随即失笑。她早该想到的——当年她在落鹰峡战死前,曾将最后半部《盐铁策》交给商队带往西域。如今,它们以琉璃灯的形式,沿着丝绸之路回来了。
“点灯吧。”她将长明灯递给江娇楚,“挂在续志祠的屋檐下。”
暮色四合时,续志祠前聚满了百姓。有人来求盐引新规的抄本,有人来拜海棠祈愿,更有老盐工指着灯罩上的刻字惊呼:“这花纹……和当年江家商队的印鉴一模一样!”
江映蓉站在人群之外,袖中拢着一把新摘的海棠果。甜中带涩的滋味漫过舌尖,像极了那些年的风雪、算珠与未写完的奏折。
6沉低声问:“陛下可要题字?”
她摇头,只从枝头折下一朵将开的海棠,别在灯架上。夜风拂过,花瓣与灯焰一同摇曳,在祠前的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远处,更夫敲响了梆子,江明镜带着孩童们念起新编的《盐政谣》。歌声混着算盘珠的轻响,飘过朱雀大街,飘向更远的州府——
那里有更多未熄的灯,正等着被点亮。
(全文终)
---
后记·灯下尘
许多年后,月影城的百姓仍记得那盏长明灯。有人说它从未熄灭,每逢春分便自动复燃;也有人说灯芯早已燃尽,但每当海棠花开时,月光照在琉璃灯罩上,仍会映出“涵”字的影子。
而史书记载,永和年间的最后一页,江映蓉只批了八个字:
“江山灯火,代代长明。”
hai